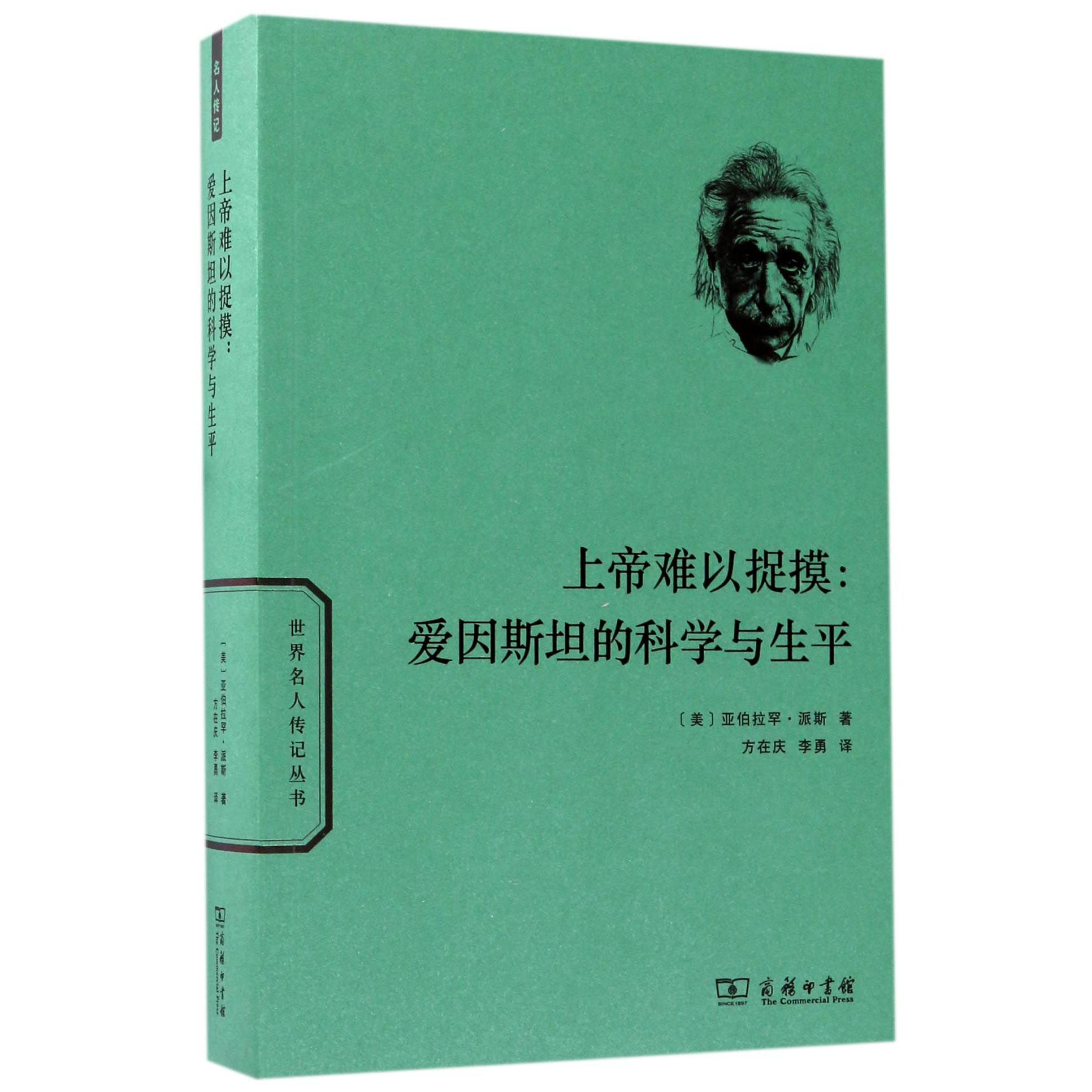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1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19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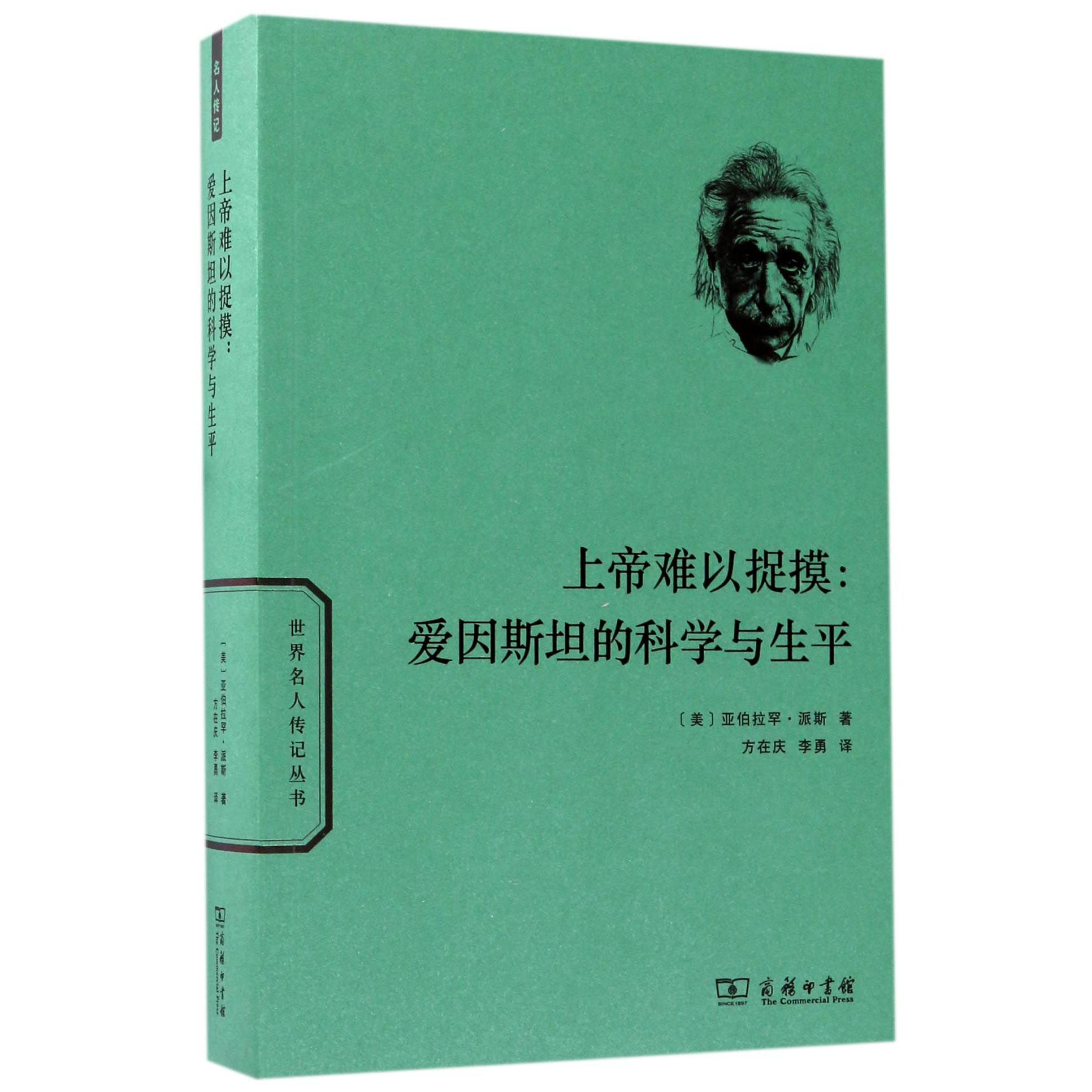
亚伯拉罕?派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在他逝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世上惟一先后同爱因斯坦和玻尔两大科学泰斗共过事的学者,也是研究他们的专家。 译者简介:方在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内爱因斯坦研究专家。有多部学术著作、译作出版。 李勇,中科院山地灾害和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有多部著作、译作问世。
为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准确,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爱 因斯坦对量子物理学的信念,还需要了解他对整个物 理学的信念。对此我相信自己是知道的,而且将尽力 在下面讲清楚。然而,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 要知道他的信仰,还需要知道他是怎样接受这些信仰 的。这一点我同爱因斯坦的交谈也说明不了什么,这 并不是他故意回避,而是我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只是在爱因斯坦去世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了答案的 端倪,那时我认识到,在现代量子力学发现近十年前 ,爱因斯坦首先认识到19世纪的因果思想将成为量子 物理学的一个严峻问题。然而,尽管我现在比同他散 步时对他的思想演化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我还是没法 说我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他坚持的那种信仰。爱因斯坦 50岁时,在给女婿凯泽尔(Rudolph Kayser)为他写 的传记的前言中写道:“也许作者忽略的是我性格中 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疯狂的那些方 面。这些方面似乎是那个永不停息地活动着的大自然 为她自己欢喜而根植在人的性格里的。但这些东西只 有在一个人的思想熔炉中才会各自显露出来。”这句 话也许对自我认识的能力太乐观了,当然,它也公正 地告诫任何一个传记作者,不要夸大地回答自己可能 会合理地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还是应该简单解释一下,我怎么会同爱因斯坦走 在一起,我们又为什么会谈到月亮上来。我1918年生 在阿姆斯特丹。1941年,在乌得勒支(Utrecht)跟随 罗森菲尔德(Leon Rosenfeld)获博士学位。后来,我 躲在阿姆斯特丹,但最终还是被抓进了那里的盖世太 保监狱。欧洲胜利日(VE Day)前夕,狱中的幸存者都 自由了。战争刚结束,我就向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 尔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和普林斯顿的高 等研究院申请博士后研究,希望跟泡利 (wolfgangPauli)一起工作。两个地方都同意我去。 我先去哥本哈根一年,不久跟玻尔(Bohr)工作了几个 月。下面的几行文字,是我对那段经历的回顾,它同 我们这里谈的事情有关。“我得承认,合作开始阶段 ,我很多时候都跟不上玻尔的思路,实际上还常常感 到疑惑。他一会儿说,薛定谔(Schr6dinger’)听说 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后,感到很震惊;一会儿又谈些 显然不相干的爱因斯坦的反对意见,我看不出它们有 什么联系。但没过多久,疑雾散开了。我开始学会把 握玻尔的论证路线和目的。像在许多运动中,运动员 在走进竞技场之前要进行热身活动一样,玻尔的头脑 中,也会再现在量子力学的内容被理解和接受之前展 开的论战。我敢说,这样的思想论战,他一天也没停 歇过。我相信,这正是玻尔之所以成为玻尔的无穷源 泉。爱因斯坦似乎永远是为他引路的精神伙伴——即 使在爱因斯坦去世以后,玻尔也一样在思想上同他争 论,仿佛他还活着”[P1]。 1946年9月,我来到普林斯顿。刚到时,我知道 的第一件事,就是泡利那时已去了苏黎世(Zarich)。 同月,玻尔也来了。我俩都参加了普林斯顿200周年 纪念大会。学者们聚在一起,爱因斯坦忽然从我眼前 走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但没看清。他正向杜鲁 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身边走去。不过,过了 一会儿,玻尔就把我介绍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友好 地向我这个敬畏他的年轻人打招呼。那次,谈话很快 就转到量子理论。他们讨论着,我在旁边听,细节已 经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个印象:他们很友 好,互相尊重。交谈热情洋溢,不分彼此。而我呢, 像第一次跟玻尔谈话那样,全然不知爱因斯坦在说些 什么。 不久,我在研究院门口遇到爱因斯坦。我告诉他 ,我不明白他同玻尔讨论的东西,问他我能不能什么 时候到他办公室去聆听教诲,他请我跟他散步回家, 这样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讨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 (P6-7) 国际流行的爱因斯坦传记,荣获198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行销全球数十万册。 编辑推荐:这部传记是世界上较流行的一部爱因斯坦传记,该传记主要特色在于相当深入地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因著者本身就是物理学家出身,且科学成就斐然,又与爱因斯坦有过科学工作合作,因此是一本权威的爱因斯坦科学工作传记。本书荣获198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还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钢铁基金会物理学和天文学著作奖;出版前10年已重印12次,行销数十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