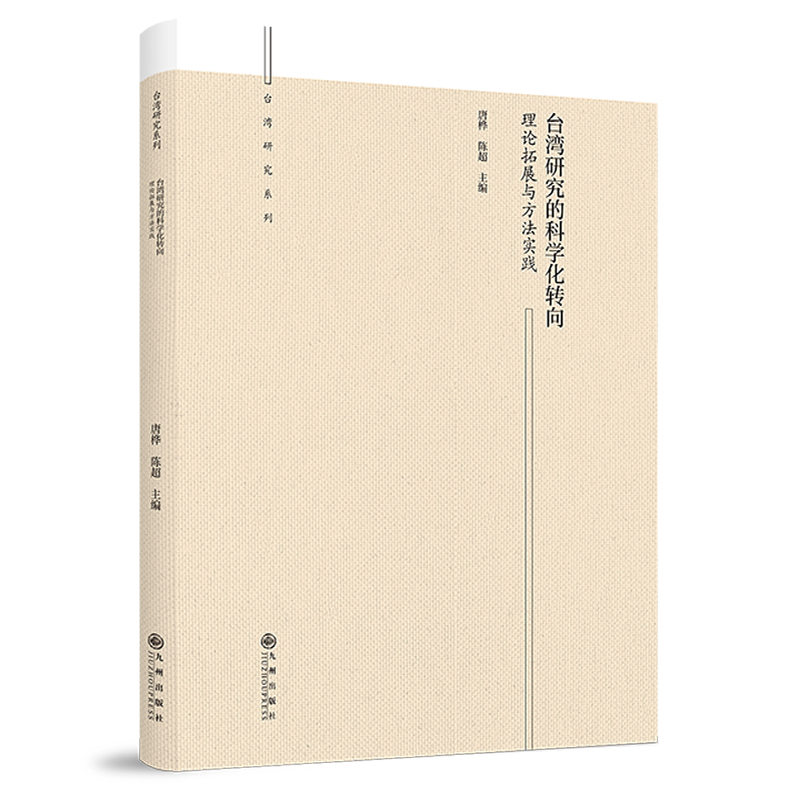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3.30
折扣购买: 台湾研究的科学化转向: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
ISBN: 9787522527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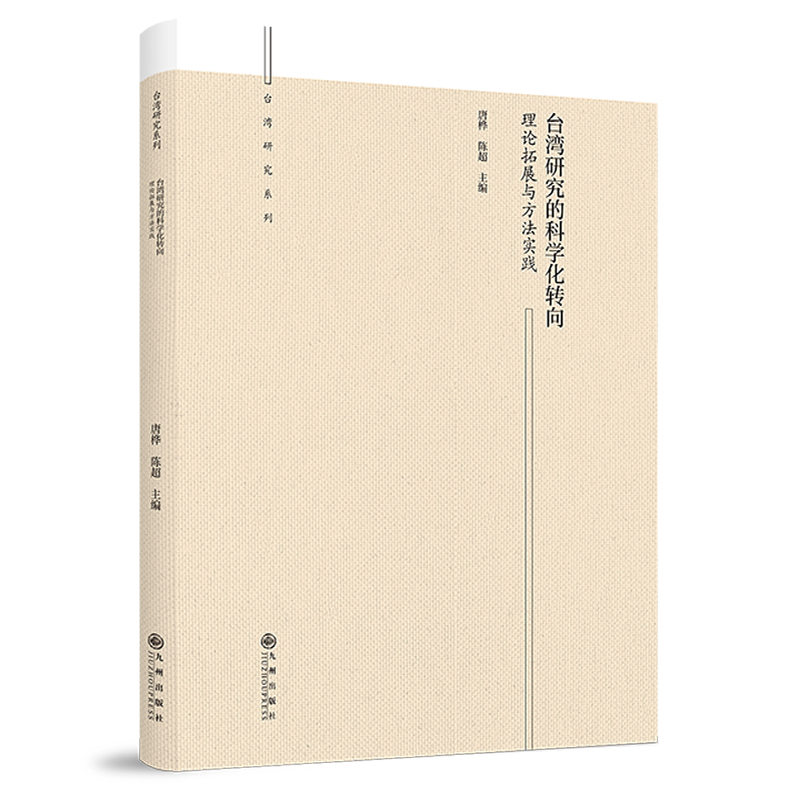
唐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温州市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闽江学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日本爱知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两岸关系、青年交流与社会融入。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和教育bu课题,已公开出版专著3部,编著1部,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多项政府部门的对策研究。个人入选“福建省杰出青年人才计划”。 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015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经济、台湾研究、案例研究方法。出版英文专著1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时间可以改变台湾青年对大陆学生的偏见吗? ——两岸青年学生群际接触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一、群际接触理论中的群际认知态度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ract theory)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由Allport在1954年首先提出,原本用于解释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在不同国家的诸多群体研究中均得到验证。该理论认为,群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歧视。这些冲突的发生正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缺乏接触。在地位平等、有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和制度支持下进行群际接触,是减少偏见的主要方式。因此,提升群体之间的友善关系,就需要给予足够的信息,而足够信息的获取,主要来源渠道之一是群际接触。 在群际接触理论中,群际认知态度指的是群体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好或者不好的评价,可以细分为表达判断、估计情况、对行为的疑问等,为进一步的群际关系发展提供机会评估。大多数情况下,群际认知态度分为正向态度和负向态度两类,也有文献在正向和负向态度之间加入中立态度,将其分为三类。Bourhis等在描述移民接收国与移民的群际认知态度时又进一步将其分为四个类别:整合(inter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离(seperation)和排斥(marginalization)。 如何测量特定群体的群内和群际认知态度是群际接触领域讨论已久的难题。Saguy等在测量群际态度时,提出的三个子问题分别面向人文素养(是否友好)、态度感受(是否尊敬对方)、人格品质(有同情心)。[类似的,在关于南非人对英国白人的群际态度和研究儿童的群际认知态度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的测量问题也都针对人格品质(是不是好人)以及态度感受(是否喜欢对方)来进行。]Zagerfka和Brown在测量德国移民后代群际认知状况时则选取自身的生活习惯、文化特质等方面来进行评判。同样以学生群体作为测量对象,Brown等在测量认知态度时,使用七分量表,测量一个学校学生对另一个学校学生学习(努力还是懒惰)、人文素养(友好还是不友好)和其他方面(体育能力高低,是否聪明)的评价。 参考上述研究文献,本研究使用了李克特五分量表来定义因变量,亦即让台湾青年自评他们对陆生的群际认知态度,1为非常不好,2为不好,3为一般,4为好,5为非常好。 二、群体偏见与群际接触 1.政治社会化、群体偏见与群体态度 社会化是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导入社会客观世界的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初级社会化是个体在孩童时期成为社会一员的第一步,次级社会化则是指将已经社会化的个人重新导入各种新的社会组成部分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民主化后台湾社会重要的形塑政治立场的解释变量。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有家庭、学校、共同团体以及大众传媒等,尤其是大众传媒可以促进公民在政治方面的兴趣、学习、效能与参与。台湾媒体普遍具有浓厚明显的党派立场,是影响民众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这一非经济学的解释理论认为公民政治行为主要由其价值与情感偏好决定,诸如意识形态、政党支持、身份支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信任等。这些内在价值认同与政治定向,经过社会政治化学习认知之后,比较难以改变。由于长期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初始印象或刻板印象多是负面、消极、贬抑的。这种负面印象当然也存在于台湾的高校学生身上。“太阳花学运”之后,两岸青年群体间逐渐形成偏见、紧张甚至敌视等心理。现有的研究显示群体偏见可以通过政治态度与初始印象情绪测量。 个体在幼年时期就已经能够形成并表现出对外群体的偏见,这些偏见可以影响到其成年之后对外群体的态度。初始印象情绪既能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接触和判断提供条件,也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偏见。对于台湾青年和陆生两个群体而言,政治态度是尤为重要的初始印象情绪或群体偏见。多年来的群际接触研究不断完善了Allport所提出的接触最优条件,其中就包括良好的初始印象情绪等。已有群际接触研究显示,众多影响群际接触的变量中,对另一群体的政治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选取最能体现台湾青年对陆生偏见的因素,即对两岸关系的态度作为研究接触态度的重要变量,并且认为更加敌对的政治态度(“台独”倾向)可能会使台湾青年对陆生的接触态度产生负面影响,而怀着温和政治态度(倾向于维持现状和两岸统一)的台湾青年会对陆生有更加正面的接触态度。 台湾民众对大陆人的初始印象情绪主要源于不同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塑造,台湾青年也不例外。在社会舆论、教育机构与媒体长期的影响下,台湾青年与陆生面对面交流之前就对陆生存在某种预设。当带有鲜明政治观点的台湾青年与陆生接触时,政治态度可能会影响台湾青年对陆生的初步印象情绪。情绪因素通常分为正面、中立和负面。负面情绪例如厌恶、憎恨、远离等会阻碍群际互动的发生,而群际接触时的正面情绪,例如认可、欢迎、赞许等,则能够有效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研究发现,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存在更积极的群际情绪态度,进而增加交流,导致更好的群际认知态度变化。英国的南亚血统群体和白人血统群体在正向的群际认知态度下,群际关系会由于自我调整而更为正面,减少了群集焦虑。Islam和Hewstone在研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信众之间的群际认知态度时选择了情绪因素作为重要变量,将其区分为:平等(完全不是→完全是)、非自愿或自愿、泛泛而交或亲密、愉快(一点也不→非常)、竞争或合作。他们发现,正面的情绪因素不但能够显著减少群际接触中的焦虑,更能够直接作用于群际态度,带来显著正面影响。DeSteno等人的研究主要针对中立情绪和负面情绪对群际态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中立情绪,生气、嫉妒、害怕、厌恶以及其他负面情绪会带来显著的群际偏见和负面认知态度。对于台湾青年与陆生之间的群际互动结果而言,台湾青年的情绪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重要正相关影响。因此,本研究以1—10分对初始印象情绪进行连续测量:1代表非常正面,10代表非常负面。本研究假设台湾青年正面情绪因素会对群际认知态度产生正面影响,而负面情绪因素则对认知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 本书对近年来涉台研究的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的科学化转向进行了集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