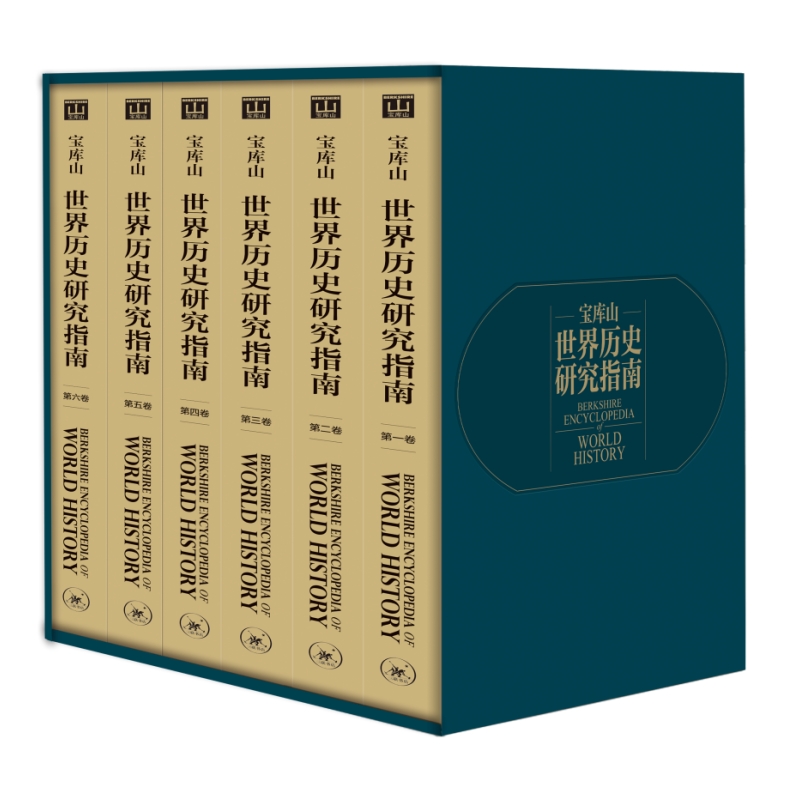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1980.00
折扣价: 1326.60
折扣购买: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ISBN: 9787108073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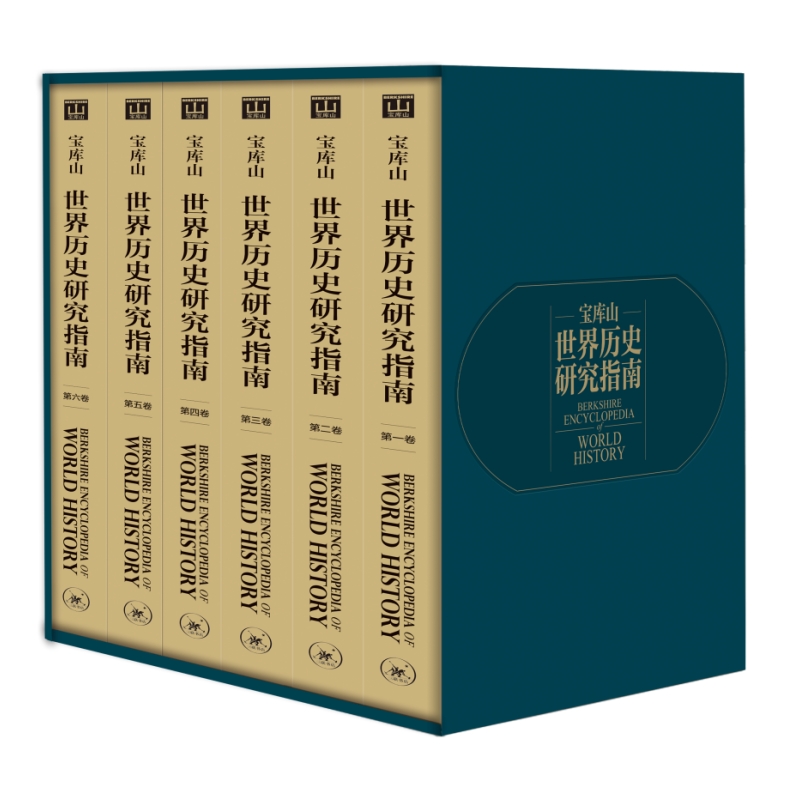
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10.31—2016.7.8),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20世纪美国学院派领袖\",\"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96年,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因其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其\"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奖章上镌刻的文字是\"扩展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麦克尼尔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泛,专著有《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合著),《瘟疫与人》《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等。
Barter 物物交换 用一种物品或服务和另一种物品或服务直接交换,其中不用到货币(金钱)这一交换媒介,这种交换行为被人们称作物物交换。由于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之间的相对价值随需求、可获取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物物交换并非天然的那么简单,而是通常会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物物交换可以被宽泛地界定为物品、服务之间的直接交换。它和有货币参与的交换行为相区分。后者在货币的参与下,可以实现购买行为与出售行为之间的分离。物物交换的观念和实践非常稳定地反映了所处社会的情境。例如,在一个太平洋岛屿上的社会里,人们所理解和践行物物交换的方式,就同当今美国社会里物物交换的做法不同。前者的物物交换可能和那些影响着某一岛屿与邻近岛屿之间关系的社交场合有联系,而后者的物物交换则可能涉及邻里之间某人为寻求水暖工帮忙而向他人让渡自己所留存的食物之事。 物物交换的特点 要想对物物交换做出任何意义上的精确界定都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物物交换通常都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尽管有许多人类学家已做出相反的论断,即物物交换总体上都缺乏社会关系)。社会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和史蒂芬·休-琼斯(Stephen HughJones)承认,任何试图为物物交换提供一种总界定或模式说明的尝试,都会造成丢失物物交换行为所处重要社会情境的损失。不过,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对物物交换行为的许多特征做出了说明。物物交换缘于人们对自己所没有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需求。例如,一个人拥有一头猪,但他可能想要一条独木船。参与交换的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被拿来进行物物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并非由货币来衡量。针对用于物物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此时还没有独立的衡量手段。交换双方必须达成协议:被拿来交换的两方物品或商品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在此过程中,讨价还价通常是关键)。最后,买与卖的行为同时发生,虽然交易的完成(交付商品、履行服务)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物物交换与经济研究 在欧洲的经济学中,有关物物交换的传统观点可以通过两个人的研究来加以理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物物交换在交换行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探讨,其探讨是现存最早的。他的解释(《政治学》第1卷第9章)对于理解一种看似可能只是简单经济行为的活动之政治与社会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在最初的人类组织形式——家庭中,并不存在交换实践,因为它是自足的,交换实践发生在更大型社会群体得以发展、家庭之间开始分享东西时。亚里士多德声明,人们对不同物品或商品的相互需求,是这些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物物交换的最初目的在于重建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自足意义上的平衡。然而,他警示道: 正是脱离了这种类型的交换,货币制造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在他不屑的眼光看来反自然的行为,因为它除了仅仅促使人们积累更多的财富外,发挥不了什么有益的作用。 在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种有关物物交换功用的更为机械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人都只生产他所需要的全部物品的一小部分,他们不得不诉诸物物交换,而“这种活动通常肯定会进行得很不顺畅,并且操作起来常让人感觉尴尬”。因为一个人不是总能找到某个人,这个人拥有他所需要的物,而这个人又希望拿自己的物和他所提供的物进行物物交换。正如斯密所解释的:我们假设,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的量多于他所需要的量,而另一个人所拥有的要少于他所需要的……一位屠夫的肉店里的肉量多于他实际所能消费的肉量,而一名酿酒师和面包师各自都想要购买一部分肉。然而,除了各自销售的产品外,这位酿酒师或面包师都没有什么可拿来进行交换的。而且,已经有人向那位屠夫提供他所急需的所有面包和啤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没有可能发生交换行为。 为了缓解物物交换所带来的不便,人们发明了货币。对亚里士多德和斯密来说,物物交换是社会发展初期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经济活动。 物物交换与礼物交换 在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带来彼此之间的接触与整合之前,物物交换在欧洲之外的许多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用途(以及不同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呈现)通常被探险者们记录下来,例如,当库克船长于1744年4月第一次造访马克萨斯群岛时,他用枪支交换别人的猪,不过他发现,猪的供应很快枯竭。在没有意识到动物在当地纪念性节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限制了出售方面的数量)的情况下,他以为是他和自己的船员们向交易市场提供了过多的枪支。 现代人类学家意识到,在商品交换和礼物交换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认为,物物交换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商品就是诸如动物或汽车等被人寻求的、既有使用价值亦有交换价值的物)。如果说商品交换的目的在于获取商品,那么礼物交换的目标则在于使收受礼物之人(或群体)心怀某种义务之感。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格雷戈里(Christopher Gregory)在一项关于此种区分的详细研究中提出,商品交换建立了一种被交换之物之间的关系,而礼物交换则建立了一种实施交换行为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此,物物交换就被判定为一种物的交换,该种交换并不通过多少陌生人之手而(像礼物那样)同社会制度(体系)相连。人们假设,在这样一些交易当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依赖关系(社会或政治义务)。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例如,在礼物交换先于商品交换的情形中,有一种关系网络将两种类型的交换连在了一起。实际上,简单的物物交换行为可能经常是人们之间远为复杂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交往过程的组成部分。 当今物物交换 在今天看来,物物交换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即便是在使用货币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尽管有亚里士多德和斯密的理论,人们还是不能将物物交换仅仅和原始经济体相连。物物交换已日益被商家所运用。如在美国,国际互惠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Reciprocal Trade Association)声明,2001年各公司之间产品的物物交换价值额度超过了75亿美元。在美国,有许多物物交换俱乐部及协会,其存在即为低水平的交易创造方便,这种交易大都包含家庭物品的交换。而且,并非所有的物物交换都和强大的经济体相连。例如,在阿根廷,通货的价值减缩、银行的关闭和大规模的失业,导致物物交换方式的使用呈增长趋势。英国报纸《卫报》(The Guardian)报道,2002年4月25日,随着现金的短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物物交换俱乐部(有时就位于购物中心之外),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将自己生产或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拿来交换。因此,物物交换是现代经济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强大的经济体还是在较弱的经济体中都是如此。 Diseases—Animal 动物疫病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引发大流行并改变社会哲学传统的疾病,均源于人类以外的动物,它们“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当我们讨论疾病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时,无须将动物疫病和人类疾病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注意到正因为人类是哺乳动物,所以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体内,尤其是在其他哺乳动物体内发现的疾病,常常会轻而易举地传播给人类,弄清并重视这一点,将是十分重要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最重大的疾病均是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甚微。依据定义所释,传染病会通过感染健康的人而迅速传播开来。被感染的人会在短时期内死亡或痊愈,而那些痊愈的人通常会获得抵抗相同疾病再度感染的免疫能力。 从数量上来看,人类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单次影响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发的流感,4000万人千年进一步提高,欧亚大陆外围国家,包括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中国汉朝,开始尝试征服欧亚内陆,开展丝绸等商品贸易活动,并尝试跨越欧亚大陆。现代名词“丝绸之路”用于描绘穿越欧亚内陆的交换网络,这个网络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联系在一起。 欧亚内陆的游牧民族国家 游牧社会的军事实力意味着其具有侵略性,能够迅速集结组成强大的军事联盟以与欧亚大陆外围强国抗衡。这个联盟的军事力量最早被农耕世界知晓,源自游牧民族军队打败并击毙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前558—前529年在位),而希罗多德对于居鲁士的继承者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在黑海草原发动的失败的战役也有详细记载。公元前2世纪,一位游牧民族首领第一次尝试组成游牧民族联盟,这个联盟存在时间很长,历史学家普遍称之为国家或帝国。这就是冒顿(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今天的蒙古创建的匈奴帝国。 欧亚内陆游牧民族国家与欧亚大陆外围的农耕国家和城市国家差别极大。其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有限,只能通过抢劫、强制纳贡、征税及贸易等手段从周围农业社会攫取资源,并在地区首领间进行再分配。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和尼古拉·迪·科斯莫曾经指出,游牧民族帝国长久存在的秘诀在于其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物质和文化资源的流动规模越大,国家就越强大;比如6世纪的突厥帝国和13世纪的成吉思汗帝国,它们崛起的基础是掠夺强大的农业国家的资源,比如中国中原政权和波斯。这也是主要的游笃会的僧侣彼得)因此丧生。据载,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瘟疫是发生于14世纪的鼠疫,西欧25%以上的人口因它丧生。不过,虽然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但是对人口和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流行病却是在美洲人接触欧洲人及其驯养的动物后不久暴发的一连串波及整个美洲的流行病。这些流行病在那些以前并未接触过欧亚疾病的人群中传播开来,尤其是在那些被殖民的过程中遭受多重创伤——暴力、被奴役、失去生计的群体中传播开来,通常会造成90%~95%的死亡率。总体看来,这些疫病有可能使美洲有多达1亿人丧生。 从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诸传染病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花、霍乱、结核病、鼠疫和流感。虽然艾滋病(AIDS)是现代世界一大潜在问题,不过它不是接触传染性疾病,也非急性传染病。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对诸如口蹄疫、汉坦病毒(Hanta virus)和所谓的疯牛病等疫病恐慌的现象,这些疫病很可能根本算不上疫病。同前文已列出的其他疫病相比,这些疫病的病理状态微不足道,然而它们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很可能是由人们对疫病的无知、媒体的宣传所激发的恐惧,夹杂着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各种疫病的转移方式等因素导致的。 大多数转移给人类的动物疫病都是由细菌和病毒引发的;这些细菌和病毒体积微小,具有高度的活性,并且能经气溶胶(aerosals)传播,因而,它们更容易从某一个体传播给另一个体,这是传染的基础。诸如疟疾和昏睡病等疫病是由原生生物、单细胞真核微生物引发的,它们的体积比细菌和病毒要大得多。原生生物所拥有的相对较大的体积意味着它们不能够经气溶胶传播,因而它们主要以注入的方式来转移,比如昆虫叮咬,这就使得它们的传染性要低一些。 大多数传染病微生物在与其他非人类物种互动的过程中共同进化。这些非人类物种会进化出对致病微生物的免疫反应,所以传染病微生物并不会对其原初宿主的健康或是种群数量造成严重威胁。对人类而言,大多数传染病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当人类首次被传染时,人类并没有进化出对这些病原体的免疫反应。比如,天花与牛痘有关,它在牛体内只产生了一点点问题,但它在人体内的变异形态对人类常常是致命的。与之相似,艾滋病毒与出现在非洲灵长目动物体内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关联密切,但对非洲灵长目动物而言,艾滋病毒仅在它们体内引发了类似于流感的微小症状。其他的例子还包括: 麻疹,它与有蹄类动物疫病——牛瘟密切相关;结核病,它与牛得的一种相似疾病密切相关;流感,它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病毒疾病,源于猪(猪流感)和诸如鸭子、鸡等禽类动物所携带的相似的病原体。近期,当人们发现引发人类疟疾的疟原虫与黑猩猩体内的一种致命性较低的寄生虫关联密切时,人们也将疟疾增补到上述类型的疫病名单中。 那些跨越物种界限从非人类物种传播到人类的接触性传染病,曾经是改变欧洲和亚洲历史的主要因素。欧洲、亚洲与美洲、非洲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欧亚文化中人们驯养动物并与之密切接触,而这些动物恰是接触性传染病的原初宿主。驯化有蹄类动物,尤其是驯化牛和猪,使人类和这些动物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使人类不断接触到各种对有蹄类动物影响甚微的流行病,人类社会中那些牛和猪饲养密度高的地区成为这些疫病繁盛的温床。农民过着定居生活,他们自己所产生的污物,以及与他们亲密共生的驯养动物所产生的污物,包围着他们。在许多农业社会里,农民习惯性地在晚上将牛和猪牵入家中。这既利于让牲畜取暖,也是为了保护牲畜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这种情况既延长了人类接触病菌的时间,也增加了病菌传播的可能性。 农业与其所取代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相比,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日益增长的城市化使人口大量聚集在一起,这为那些源于其他物种的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沃土。欧洲的城市仅仅是在20世索过一天可以被分割的最小时间单位是什么,但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复活节日期的计算。另外,阿尔马的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 of Armagh)大主教在1650年左2510右推测出, 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是基督诞生前4004年的10月23日,周六下午6点。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年代学含有更长一些的时期单元,例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玛雅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时间周期,但是这些数字仍然属于短尺度日历的简易数学级数。 今天时间区间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宽了。现代技术也能更加精细地分时: 比赛计时可以精准到千分之一秒级;全球的原子钟同步运行,误差可以减少到十亿分之一秒;而最快的激光脉冲又为时间尺度缩小到飞秒(femtosecond,千万亿分之一秒)提供了可能。在\"深邃时间\"的领域里,宇宙的寿命据认为有大约130亿年,地球的年龄大概有45亿年,人类的祖先出现于700多万年前(随着新化石的发现这个结论可能还会变化)。这些数算得益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和宇宙论在近200年里的发展。 个人时间 19世纪晚期,科学家开始试图解释我们个人时间意识的生理过程。并且在解释人类生理周期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昼夜节律--也就是接近一天的生命周期。我们用这种知识为我们服务,比如药物治疗的效力在一天中是在不断变化的。支撑大量个人\"时钟\"的细胞和生理过程也正在敞开它们的秘密,例如人们已经了解到身体机能与环境同步的机制(内置时钟)以及估测逝去时间的独立计时器(内置码表)。神经学研究能够识别对人类记忆十分重要的脑区,在这片脑区里,时间印记(time stamp)与具体的事件附着在一起,而基于这些时间印记的时间次序就可以被储存和检索。 不过,真正理解人类的时间意识--特别是我们主观感知时间流逝的速度存在极大差异--仍然有困难。而且格外讽刺的是,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偏离自然周期的时候--比如,倒班、24小时的购物、空调系统和电气照明紊乱了人与环境时间的联系--我们才幡然醒悟。 未来 我们测量时间的技术在以近乎指数增长的速度进步。现在的一天与往常是一样的长短(至少非常接近),但快速的社会变迁使我们常常感到捉襟见肘、时间短促,所以时间变得更加宝贵。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从钟表时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呼唤早在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那时起人们不断发出这种声音,现在做的仅仅是重复而已。 时钟已经成为很多现代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从电子通信到电子商务,到电力分配,再到卫星导航。我们把精确地掌握时间当作理所当然,但是时间最终还像以前那样神秘。正像社会学家米歇尔·扬(Michael Young)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欺骗自己说知道什么是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可以确信,未来的时间与过去一样,仍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纪时才真正实现了人口自我平衡,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有太多城市居民因疾病而丧生,以致必须从乡村地区不断往城市迁徙人口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 黑死病 世界商路的发展加快了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古罗马时代,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人群逐渐成为滋养那些源自家畜的疾病微生物的巨大温床。2世纪时,天花肆虐罗马,引发“安东尼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数百万的罗马市民在瘟疫中丧生。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对欧洲和亚洲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动物疫源性疾病。该病通过跳蚤传播,跳蚤从鼠疫通常的宿主即毛皮动物那里感染了鼠疫杆菌。542—543年,欧洲发生了“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这是鼠疫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不过,直到14世纪,欧洲大陆才出现了最具毁灭性的瘟疫,它造成欧洲大陆多达2500万人丧生,并逐渐被人们称为“黑死病”。仅大不列颠群岛,瘟疫就造成近1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40%)丧生。随着14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之间开通商路,毛皮被人们从中亚的人口低密度地区带到欧洲,而这些毛皮似乎是导致大型瘟疫暴发的病菌的主要携带者。 14世纪的这场瘟疫产生了一个重要却常让人不以为意的后果,即它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科学。14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盛行的世界观是神秘主义的和象征主义的,植根于循环时间观。与黑死病到来之后兴起的世界观相比,这种世界观更强调人类和世上非人类因素之间的联系。 当瘟疫降临并开始给所及之地的人们造成巨大灾难时,这种旧哲学传统下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被用来为人们提供帮助,包括祷告、基于交感巫术的医治和寻找替罪羊(比如焚巫)。然而,这些方法中没有一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此外,在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破坏面前,人类的无能为力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慌和继之而来的文明大衰落。疾病造成了大量的、不明原因的死亡,这对社会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算都不为过。传统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对世界运转方式的固有理解被彻底粉碎,以致产生精神空虚感。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瘟疫视作“历史上最重大的生物-环境事件”,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称其“相当于核灾难”。这场瘟疫迫使西欧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建构现实认知。在基督教的世界里,瘟疫使人们失去了对仁慈的、怜悯的造物主的信仰;使人们将“异教徒”作为替罪羊来加以迫害;最终,它促使了新教的诞生以及新教中开始有了一个愤怒的、复仇的上帝形象。 从一个更为学术的角度来看,经历瘟疫,人们的知识传统得到发展,即身与心分离、客观与主观分离以及人类与自然分离。这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以及西欧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传统的发展,并最终生成为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一种以机器模型或隐喻来理解非人类世界的方式,以及培根-牛顿世界观。因此,瘟疫给哲学和精神信仰带来的影响直接促成了“现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出现,在这种方法中,实验和测量代替了原来的观察和经验。 这种认知现实的新方式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比如,卫生条件变好,这使许多接触性传染病的发生环境得到净化。这种将现实世界分离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方法,为研究和理解“外在的”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不过,这种方法并不足以理解内在经验、人类的心灵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二元论观点虽然促使卫生条件提高,但并未加深人们对疾病自然周期或免疫反应进化等问题的理解。 旧世界和新世界 通过将旧世界(欧亚和北非)与新世界(北美和南美)进行对比,我们将明了动物疾病在塑造人类历史和人类对待环境的文化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美洲的许多文明中均有农业,不过,新世界的农业几乎完全建立在以种植诸如玉米、马铃薯、美洲南瓜和豆类作物等为主的农业基础上,而不是以游牧业、畜牧业以及驯化有蹄类动物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美洲的驯化动物有狗、豚鼠、原驼(美洲驼和羊驼)以及火鸡。与旧世界驯化的有蹄类动物不同的是,新世界的驯化动物的饲养密度一直不高。人们既不饮用动物奶,也不同旧世界那般,将驯化动物作为家畜来饲养并与之近距离接触,唯一的例外是狗。 新世界许多文明的人口密度也很高,与欧洲不相上下。鼎盛期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有可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证据表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的长期环境承载力。与之相似,同欧洲和亚洲已知的人类文明相比,新世界许多其他的文明区域比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以及生活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筑堤人(the Mound Builder)文明等所建立的城市,均有着与已发现的欧亚文明中的城市可比拟的人口密度。不过,新世界各文明的人口密度虽然很高,但在这些土生土长的新世界文明中几乎没有流行(群发)病,这无疑得归因于新世界文明中缺乏已驯化的有蹄类动物,正是这些动物在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成为大多数流行病(鼠疫除外)的病源。新世界虽没有流行病,但流行病却很可能与美洲一些大型城市的消失有关,这有可能是由当地卫生条件较差而导致的。 新世界的动物疫病 动物疫病史上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之一乃是,新世界并不存在非人源接触性传染病且缺乏相应的免疫力,而这几乎肯定恰是欧洲人及其世界观——仅在数世纪之前因亲身经历接触性传染病而被重新锻造——成功入侵美洲的重要因素。欧洲人曾时不时地占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地区,不过,由于他们所带去的传染病没有对当地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当地人口并未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大量减少。 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依然保持了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因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非洲和亚洲的土著居民重拾了在自己土地上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相比之下,对美洲土著居民而言,欧洲人所带去的动物疾病给当地易感染人群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远甚于瘟疫在欧洲造成的损害。据估算,美洲90%~95%的土著居民死于外来疾病。 与盛行的说法相反,这场被认为是欧洲人征服美洲的第一阶段或微生物阶段的浩劫并非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而是肇始于更早以前。当巴斯克捕鲸人(Basque whalers)、维京移民和英国渔民开始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登陆时即已开始。这比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和其他西班牙探险者(征服者)抵达新世界的时间早了数百年。有证据表明,早在15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一些原本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部落曾退居内陆,以此逃离那夺走大部分人性命的流行病。 虽然科尔特斯(Hernn Cortés)和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等所谓的征服者曾在美洲获得成功,但是天花才是使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崩溃的真正元凶。科尔特斯于1519年初次远航并入侵阿兹特克文明所取得的成功,远不如他在天花传播至特诺奇蒂特兰之后的1520年的再次入侵。至17世纪初,墨西哥超过90%的土著居民死于天花,人口数量从2000万左右跌至不足200万。疾病使阿兹特克人士气低落,失去了抵抗科尔特斯的能力。与之相似,天花于1526年传播至印加帝国,为皮萨罗1531年的成功“入侵”提供了契机。 已知的证据表明,欧洲人及与之共生的其他物种在抵达美洲时所带去的新型传染病,使90%甚或更多的土著居民丧生一个广为记载的例子是,超过95%的曼丹人(the Mandans)——北美大平原诸文明中最精致复杂的文明之一——在天花于1837年经密苏里河的船只传播到当地之后,染疫而死。不过,即使造成了这些后果,如果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欧洲人入侵之后没有被永久占领,没有随后持续实行的殖民统治,那么,新世界的人口仍可能出现回升。 外来疾病的传入,对美洲土著居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如果说瘟疫在造成欧洲20%~40%的人口死亡后,就已经促使人们重构和重新思考人类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当瘟疫使美洲诸土著民族90%~95%的人口丧生时,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宗教、社会和哲学影响。 虽然疾病是限制人口增长率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未受疾病影响的人口数量通常都超过那些遭受疾病影响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前,相对而言,当地土著居民未受到过传染病的影响。因此,土著居民未能形成抵御传染病的免疫力。当地土著居民其实并不缺乏生成免疫反应的能力,他们传染病的方式似乎才是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原因。导致美洲土著居民死亡的主要杀手——天花和流感,主要会对那些15~40岁的人造成致命影响。从文化和人口学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人口中最有价值、最有生产力的人。这些传染病通常集中暴发,它们会因暂时的缓解和其他小插曲而间或被打断。因此,人口聚居区很有可能是因为一连串的三四种疫病的肆虐而被毁灭,接着是一段缓解期;随后这些人口聚居区很可能又受到另一种或者一连串新疫病的袭击。这种大量疫病混杂在一起周期性到来的情况,削弱了美洲土著居民进化形成免疫反应的能力。 这种疫病传播模式给当地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人们无力阻止疫病的肆虐,无力照顾自己及亲人,病患被那些逃离疫病的亲人和部落其他成员所抛弃(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将疫病传播到其他民族和聚居区),完全放弃了希望。人们所采取的许多治病方法,比如出汗后随即浸泡于冷水中等,只是加速了死亡。所有的传统疗法在治疗和控制这些传染病时失去功效,这使人们不再信任治疗师和巫医,同时也放弃了传统的灵修活动和仪式。由于欧洲入侵者们已具有某些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许多土著居民认为欧洲的精神信仰和哲学传统比他们自己的要好,这促使许多土著居民接受和信奉了基督教及其教义。 土著居民信仰传统的衰落,加上新货物和原料进入美洲,使得土著民族放弃了自己在与自然世界打交道时曾以尊重自然、与自然相联、保护自然为基础而形成的悠久传统。有些土著居民甚至有可能因传染病而责难野生动物和自然界,这是因为似乎许多土著居民都将疾病的产生与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在他们看来可以将疾病的影响和发生疾病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的文化传统。比如,切罗基人(the Cherokee)认为杀鹿是一件不敬之事,这有可能产生像莱姆病(Lyme disease)这种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疾病。切罗基人将新疾病的出现归咎于宇宙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是他们未能正确遵循古老仪式所引发的。与之相似,阿尼什纳比人(the Anishinaabe)(亦称齐佩瓦人[Chippewa]或奥吉布瓦人[Ojibway])中出现了大药师会(Mediwinin healing society)和相关的仪式,以应对一些在他们看来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疾病。不过,这些疾病更有可能是在前哥伦布时代他们与欧洲人接触时所感染的。 对人类以外其他物种的影响 人类并非唯一承担上述外来疫病侵扰的物种。18世纪下半叶,那些生活在哈得孙湾以西到落基山脉间并成为土著居民生存之衣食来源的野生动物种群,包括鹿、驯鹿、驼鹿、野牛和河狸也大量死亡。它们之所以死亡,很有可能是欧洲人带到美洲的驯化动物所携带的疫病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动物们相继死亡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有蹄类动物中,它们很可能是最易受到欧亚地区有蹄类动物携带的传染病感染的群体。新世界的食肉动物比如狼和熊等,相对而言似乎不受这些疾病的影响。不过,它们面临了有蹄类动物数量减少所造成的食物来源减少的问题。 除了疫病的上述影响外,当土著居民抱着明显厌恶的态度去消灭动物时,野生动物的自然群体遭受到了另一重打击。人们认为是这些动物将疫病传染给人类而破坏了它们与人类的盟约。因此,非人源接触性传染病被传入美洲所造成的一个讽刺性后果,乃是以尊重非人类物种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摧毁。即使不是全部的北美土著文明,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曾拥有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即认为非人类物种亦有灵,并以生态关系为基础形成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休戚与共的观念。有人认为,外来疫病对这些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致使人们转而向其非人类伙伴发动攻击,这就使一些部落为了与欧洲人进行皮毛贸易以换取其商品和金属,而将当地的河狸、鹿、野牛和狼等种群猎杀殆尽。 欧洲传统和自然世界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那些入侵美洲的欧洲传统与美洲的截然不同,这种欧洲传统主要源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文化,但它更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物;这种欧洲传统致力于将人类自身与自然界完全分离开来,只有在将自然界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时,二者才产生联系。文艺复兴末期(宗教改革期间),西欧基督教的新教教派所发展的哲学传统并不鼓励人们去探究上帝造物的方法。上帝让人类“凌驾”于非人类世界之上,这就为人类可以任意地对待自然界提供了足够的正当性。 在欧洲人眼里,山区意味着不愉快、危险,而森林则更危险。这些地方是野生的,因而它们是未被驯服的,这便足以引发西欧人对之产生恐惧和敌意。荒野(自然世界)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使人们对那些进入人类领域的野生动物保持着高度警惕。一只蜜蜂飞入村舍小屋,又或是一只鸟在窗户上轻敲,都足以让人们惊恐。1604年,英国下议院之所以拒绝通过某项议案,就是因为提案者在进行发言陈述时有一只寒鸦曾飞过议会厅。 即使是在今天,人类差别对待非人类(自然)世界的态度和行为继续存在于人类应对动物疫源性传染病的过程中。同疫病真正带来的威胁相比,这些应对措施常常是极端的、过度的。近些年来最过激的应对举措是欧洲人屠杀了几十万头农场动物,这在大不列颠群岛尤为严重。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小规模暴发的口蹄疫,以及零星发生的所谓的疯牛病。 就口蹄疫而言,它几乎仅是对经济造成冲击,鲜有证据能证明口蹄疫会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不过,口蹄疫对经济造成的威胁仍足以成为人们屠杀数十万头动物的理由,这通常是因为人类有可能接触到这种疾病。如果动物们所接触到的潜在疾病传染源是智人而不是有蹄类动物,那么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是否还能够想象出我们用这样一种残酷的屠杀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场景?与之相似,那些走到美国黄石公园边界外的野牛常被蒙大拿州的一些部门立即屠杀掉,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这些动物有可能是牛科疾病布鲁氏病菌的携带者。讽刺的是,布鲁氏病菌是在旧世界的牛科动物体内进化形成的,并随着旧世界的牛一起传播至美洲。美洲野牛从未出现过感染布鲁氏病菌的症状,然而,小部分美洲野牛在病原体检测中呈阳性的事实仍足以成为人们屠杀美洲野牛的理由。 人们在应对疯牛病——更确切的名称是牛脑海绵状病(英文简写BSE)——时采取了更为荒谬的措施。疯牛病是由朊病毒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病症中的一种,朊病毒似乎是一类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分子。其他同类型疫病还有羊的痒病以及人类的库鲁病和克雅氏病。这种病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逐步损毁大脑。人们根据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后牛科动物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轻蔑地称之为疯牛病。不过,一个比该名字更恰当、更精确的名字应当是“极痛苦的牛”。这些明显是因朊病毒作祟而出现的病症不会以接触的方式直接传播,而只能通过食用中枢神经海绵组织的方式传播,这些中枢神经海绵组织包括脑和脊髓。这种病症之所以在美国和英国广泛传播,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屠宰场会在屠宰动物后将“动物废料”粉碎,并把它作为一种蛋白质辅料添加到牛饲料中。 很明显,人类只有在食用含有牛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食物后才有可能感染该疾病。新几内亚之所以会暴发库鲁病,与其食用他人脑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英国,那些食用过劣质汉堡的人曾出现过疯牛病般的症状。显然,如果能在供人类食用的汉堡和牛的饲料中禁止使用屠宰场的动物废料,则能避免引发该病。然而,这种调整却因经济压力而进展缓慢,甚或被阻碍。不过,世界上得疯牛病的人数量不足20人,人们用烤或煎的方式来烹煮牛肉,一般不大可能感染该病,该病也不会在人类中暴发。 汉坦病毒是一种啮齿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鼠科啮齿动物身上都携带有一系列类汉坦病毒。有一种被称为汉坦病毒的病毒,似乎仅将一个物种——鹿鼠(deer mice),又称为鹿白足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作为其主要宿主,不过,它在鹿鼠体内似乎并未引发重大的健康问题。然而,这种病毒会在人体内引发类似肺炎的症状,致死概率达50%。对美洲西南部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种他们十分熟悉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也很有可能是迪内人(Diné,又称纳瓦霍人[Navajo])会毁掉过世之人曾住过的泥盖木屋的原因。近些年,这种疾病在美国引发小规模的恐慌,因为鹿鼠是一种分布广泛且十分常见的啮齿动物。由于汉坦病毒似乎不能在人类中传播,所以它不可能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流行病。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开始记录相关病例以来,在美国已登记在册的病发案例不足200起。 人类世界中那些与环境、健康相关的问题,基本上都源自人类与驯化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这种长期的亲密接触使一些疫病能够跨越物种之间的壁垒,从其有蹄类宿主或禽类宿主那里转移到人类身上。 Eurasia,Inner 欧亚内陆 欧亚内陆特指一个广阔区域,包括中亚诸国以及蒙古等地。这个区域地势平坦,因此那里的国家幅员辽阔;流动的生活方式和游牧社会也因此具有重要地位,贯穿该地区从狩猎-采集时代直到今天的历史进程。 欧亚内陆只是这个地区的多重地理标签之一,源自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历史。欧亚内陆这个最核心地区还有其他称呼,比如突厥斯坦、中亚、欧亚大陆中心和亚洲中心。欧亚内陆这个名词涵盖范围最广,它将亚洲中心地区与蒙古和俄罗斯连成一体,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也因欧亚内陆独特的地理特点形成自身特色。 谨慎精确地使用这些地理名词在方方面面的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世界历史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地理名词反映了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独特视角研究历史。如果不加分辨地利用这些名词,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将会扭曲,我们会以今天的眼光看待遥远的过去。谨慎准确地使用这些名词,它们将揭示崭新的历史画面。地理学家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曾经指出,元地理学,或我们研究世界地理的学科,在绝大多数层面上决定了历史研究课题。比如,传统上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界线是乌拉尔山脉,因此理所当然地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认为所有的亚洲社会都有相似性,乌拉尔山脉和黑海一线是这些元区域的断层线。直到今天,这些观点也没有经过审慎评价,但是这些名词对于不明所以的读者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陷阱。 对于欧亚内陆的描述 欧亚内陆特指一个广阔区域,包括中亚各国以及蒙古等地。将这个辽阔分散的区域连在一起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欧亚内陆在地理上接壤,其历史进程具有统一性。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指出,将欧亚大陆分为两个主要区域更加适宜。因为其中心地区是极其辽阔平坦的平原——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平地。欧亚内陆主要由两个古老板块组成,这两个板块于大约3亿年前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山脉,并从此与低矮的乌拉尔山脉分离。在欧亚内陆平原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分布着众多次大陆岛屿,地形特征各不相同。这些地方构成我们所称的外欧亚大陆。外欧亚大陆包括欧洲和亚洲西南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中国。现代欧洲和中国所在的板块在大约2亿年前与西伯利亚板块连成一体。 在过去的6000万年里,今印度和非洲所在板块向北移动,与欧亚板块碰撞,形成从阿尔卑斯山至喜马拉雅山一线的山脉。这些山脉成为欧亚内陆和外部的分界线。因此,普遍认为欧亚大陆为一个古老的内陆平原,其周围是一系列沿海区域,地形更加起伏复杂。 从大的方面看,欧亚内陆和外欧亚大陆差异极大。不仅在于内陆比外围更加平坦,也因为其与海洋隔绝而更加干旱;只有在北方,极寒气候限制了蒸发和沉淀的过程。在欧亚内陆,只有最西部(今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部和俄罗斯欧洲部分)、西伯利亚东部沿海的南端以及西伯利亚中部,年平均降水量超过500毫米。而在外欧亚大陆,很少有年平均降雨量低于500毫米的地方;在许多地区,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其原因是欧亚内陆地处北方,光合作用较弱。欧亚内陆的平均气温低于外欧亚大陆。麦金德(1962)曾经指出,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一般在1月结冰:“在严冬季节,从月亮上看去,白茫茫一片,仿佛巨大的白色盾牌遮住中心大陆。”欧亚内陆十分平坦,大部分地区远离海洋湿润气候的影响,其气温变化较外欧亚大陆更加剧烈。其冬夏温差明显,在东部尤为突出,因此,蒙古的气候环境比乌克兰更加恶劣,变化也更加剧烈。 地势平坦、气候干燥、纬度靠近北方、大陆性气候,这些特征塑造了欧亚内陆的所有社会,也导致欧亚内陆与外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迥然不同。地势平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区出现的国家位列世界面积最大国家之列,因为这里没有天然屏障阻碍大规模军队调动。恶劣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欧亚内陆的人口密度小于外欧亚大陆。这种现象甚至在人类四处游荡的时代(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因为人类在非洲大草原起源,为了能够在欧亚内陆地区生活,必须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发展新型狩猎技术。在过去的2000年时间里,欧亚内陆与外欧亚大陆的人口差距已经从1∶10上升到1∶20,尽管两者的面积几乎相同。正因如此,欧亚内陆人类定居的时间似乎略晚于外欧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由于气候干燥,几千年的时间里该地区农业发展缓慢;只有在今乌克兰部分地区和中亚边境地区,由于具备灌溉农业发展条件,才有所进展。大型农业社会出现在乌克兰的特里波利耶(Tripolye)文化和中亚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社会出现在公元前第3个千年。在其他地方,农业革命的进程几无二致,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占据欧亚内陆大部分地区。可以说,在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农业文明发达、众多主要农业文明形成的时期,欧亚内陆农业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欧亚内陆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反而体现为游牧的生活方式。 游牧的生活方式 农业生活方式以种植植物为主要特征,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则表现为驯养牲畜。游牧生活方式的形成有赖于一系列的发明创造,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称其为“次级产品革命”。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人类开始开发新型畜类产品,不仅生产屠宰动物产品(皮、骨和肉),也开始开发二次产品,比如毛、血、奶和牵引畜力——这些是能够保证在牲畜存活的条件下获得的产品。这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驯养家畜的使用效率,而围绕着驯养家畜——比如绵羊、 牛、山羊、马、骆驼和牦牛——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得以建立。游牧生活方式证明,在从匈牙利延伸出来的广袤草原上,有可能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游牧生活是这个地区的主流生活方式。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游牧生活证据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文化,该文化保留了最早的骑马证据。该文化时期人类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是在公元前第3个千年,游牧生活的部分方式扩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大部分地区,并且影响到今哈萨克斯坦。草原墓葬遗址发现的证据表明,游牧生活方式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并且成为一种生态现象,因为放牧大群牲畜的经济生产方式需要在广大区域内流动。公元前2000年,游牧生活的部分方式已经扩散到蒙古的西部边境。专门从事欧亚内陆研究的学者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o)指出:“保守观点认为,西亚和中亚骑马民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公元前第3个千年中期和前第2个千年早期。”公元前1千纪,游牧生活方式终于传播到蒙古地区。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新颖的、尚武的欧亚内陆居民使用多种牲畜运输。这幅照片摄于20世纪初,骆驼身上驮满货物特点,如新型马鞍和性能优良的组合弓等的使用。 欧亚内陆大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对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到该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游牧生活无法养活农业文明那样众多的人口,游牧者通常处于流动或半流动状态,因此游牧的生活方式不会创造出欧亚大陆外围地区那样密集的聚落。这个地区的大半部分没有市镇和城市。小规模的、流动的营地取代村落和城市成为草原的主角。因为城市及我们所认定的城市和农耕文明的要素仅在欧亚内陆的部分边缘地区发现,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欧亚大陆外围区域迥然不同。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差别是游牧社会保留的文字记录较少。因为历史学家十分依赖这类记录,所以他们相对比较忽视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也因为如此,我们对于这些社会的认识是通过欧亚大陆外围农耕文明的视角,即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部分描述。即使最为公正的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史学家也将欧亚内陆视作一个黑洞,这里出来的游牧者骑马抢劫、掠夺“文明”世界的村庄和城市。在世界历史记录中,欧亚内陆居民长久以来被视为“蛮族”,这并不奇怪。 部分原因是游牧民族具有流动特征,他们的技能是驾驭大型动物,他们娴熟的骑马技能保证了欧亚内陆社会拥有巨大的军事影响力,而与绝对人数多少并无多大关系。对于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司马迁有过精彩描述: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 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Watson 1961) 骆驼可以很轻易地运输蒙古包——方便携带的木架披毡式房屋——穿越草原。因此,蒙古包成为流浪者和游牧民族的最佳居所。关于游牧社会有限的记载证明,他们通常与周围的农业社会进行交换活动,出售肉、皮、布匹等,获取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包括武器。有证据显示,这些产品交换活动有些是和平的,但是有些是暴力抢劫的。早在公元前4千纪,在乌克兰特里波利耶文化边缘地带,就已经有这些活动的证据出现在草原墓地遗存及农业社会日益普及的防御工事遗存中。 欧亚内陆的文化交换 游牧民族流动及热衷交换的天性导致了商品、思想观念、人口和各种影响在欧亚内陆草原迅速扩散,其速度超出想象。游牧民族将游牧生活技术传播到草原边缘地区的中国。 他们同时传播着语言。印欧语言在整个欧亚内陆以南地区传播,主要传播者是游牧民族;大约2000年前,突厥语开始向东传播,主要传播者同样是游牧民族。另外,游牧社会也充当了宗教、艺术和技术——比如青铜制造工艺和战车——的传播媒介。欧亚内陆草原不是文明的壁垒;相反,最晚在公元前第2个千年,它已经成为连接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纽带,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欧亚大陆内陆和外围已经形成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欧亚联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的奥克苏斯文明(位于今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考古学家在这里既发现了来自草原的商品,也发现了两河流域、印度,甚至中国的商品。欧亚大陆间交换的重要地位在公元前第1个牧民族国家沿欧亚大陆内陆和外围边缘地带兴起的原因;也因此,许多强大的游牧民族领袖,比如12世纪的塞尔柱人和16世纪的莫卧儿人,跨境在欧亚大陆外围附近区域建立了王朝。 欧亚内陆的农业 欧亚内陆游牧生活方式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欧亚内陆及其外围区域创造出了复杂的共生关系,并且持续了几千年。但是在过去1000年里,欧亚内陆游牧生活方式占据的统治地位遭到来自西方的农业社会的严峻挑战。公元第1个千年中期,大批来自东欧的农民开始在乌拉尔山脉以西定居,这个区域今天属于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俄罗斯西部。农民在远离这个地区几千年后又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黑麦种植以及金属工具日益普及有关;这些进步有助于农业生产适应欧亚内陆西部恶劣的气候环境。哈扎尔人(Khazar,7—10世纪兴起)等草原统治者开始从这些社会榨取资源;维京武士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稳定的农业国家,组成城市国家联盟,由维京人领袖统治,时间大约在10世纪。 农业在欧亚内陆出现后,日益成为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主要支柱,成为人口和经济的基础,而这是游牧社会无法企及的。农业不仅造就了罗斯和立陶宛国家,也支撑着蒙古帝国的残余势力,比如金帐汗国(13—15世纪)。莫斯科公国建立后控制了欧亚内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国家逐步控制了西伯利亚森林地区,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农耕国家。农业人口日益增加,农业国家绝对的人口数量保证了它们在与周边游牧社会对抗时占据优势,并持续了几代人。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公国和沙皇俄国也开始觊觎欧亚内陆草原。19世纪末,沙皇俄国已经征服了草原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中亚。与此同时,中国清朝军队已经征服新疆,它战胜了最后一个游牧民族大帝国,即准噶尔,并控制了蒙古大部。游牧生活方式的统治地位丧失,欧亚内陆与欧亚大陆外围一样处于农业国家统治之下。 但是,欧亚内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在该地区如今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业国家留下印记。欧亚内陆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农业生产比较艰难,很难达到欧亚大陆外围地区的农业产量。因此,欧亚内陆的农业国家热衷于运输资源,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领袖必须十分强势、专制。与此同时,平坦的草原也将农业国家和游牧国家置于冲突的前线,迫使它们高度重视武器资源。但是这也让它们有可能建立大型国家,因为地理条件导致天然屏障薄弱,无力抵御强大国家的扩张。这可以解释莫斯科公国和沙皇俄国的历史为什么被认为是缓慢占领欧亚内陆的历史。最后,以欧亚内陆相对恶劣的生态地区为主要领土的俄罗斯国家具有流动传统,这可能也可以解释苏维埃执政时期的经济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原因。苏维埃国家与莫斯科公国和沙皇俄国一样,有能力控制大规模资源的流动。从这个角度看,欧亚内陆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地区从狩猎-采集时代直到今天的历史。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of 语言的标准化 语言的标准化是创造某种形式的语言的过程。这种形式是讲这种语言的人们喜欢的形式(通常是书面形式)。这个过程与世界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在一个地区占据特定地位的语言拥有一种潜能,使一些人边缘化,并使其他人享有特权。征服者经常贬低被征服者的语言,而恰恰是这个被贬低的语言,能够成为民族运动的聚焦点。 语言的标准化常常是有意识地实施的,有时是详细规划的过程,旨在创建一种语言——通常是书面形式——使其成为讲这种语言的人们接受和喜欢的交流方式,这些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使用这种标准语言或多或少变形了的语言。典型的语言标准化机构在政治社会(通常是国家)的范围内及其支持下运作,但也有一些有意识的语言标准化活动在没有这种支持,甚至反对国家权威政治愿望的情况下进行。 语言变体的本质 人类语言持久性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变体。语言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很多人讲的语言经常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相异性,这有时会妨碍生活在不同地区但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进行有效交流。没有两个人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这或许是安全的说法。社会语言学家(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的人)讨论不同的个体方言,即单独的个人使用的语言。为了将语言作为有效的交流工具,大量个人使用或能够使用一种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的语言(或一个变异语言,更中立的称呼是语言密码),这当然是必要的。这种一致性能够使讲话者与其他讲这种语言的人进行有效交流,足够理想的状态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在初次见面时就能够毫无障碍地交流。一群使用这样一种语言变体(任何群体成员获得的并将其作为一或本土语言的语言)的人可以称为语言集团,而他们的语言变体可以不太严格地被称为一种语言。大区域内的大语言集团使用的语言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域变体。区域变体(其特征可能是所有语言分系统中存在语言差异,例如语音、构词、句法和专门词汇)通常被视作方言。大多数语言集团是足够大的,人们从中可以识别出某种程度的社会差异或社会分层。这些语言的变体依靠社会边界划分,从而这些变体被称为社会方言。一个较大的语言集团的普通成员是一个方言的典型本土人,在适当的地方也能够使用社会方言。正常情况下,很多个人能够使用或至少能够理解较大语言集团的其他方言或社会方言变体,尤其对于那些具有高度地理或社会流动性(或两者都具备)的个人来说。 把方言与语言区别开来并非易事,而且区分结果常常是根据非语言标准做出的。例如,冰岛语言边界的确定根本没有问题。它是冰岛人口唯一的本土语言;它的内部方言差别是很小的,冰岛以外的任何本土人都不能用这种语言。然而,欧洲大陆的一些语言并不能这样直接界定。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由低地德语和荷兰语形成的语言对比: 分布在从佛兰德斯地区到德国东北部的欧洲西北部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两端的讲话者很少或几乎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彼此进行交流;当各自向荷兰和德国边境移动的时候,实际的语言差别大大消失了;而在边境地区,两边的人讲的方言足够接近,以至于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这样的区域通常被称为方言连续区: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语言差别逐渐增大。边界一方国家讲的语言变体被视作荷兰语的方言,而边界另一方讲的那些语言变体被称作(低地)德语的变体,这种事实不是以语言学的理由为判断标准的,而是政治考虑或语言标准化的结果。有时因为历史和政治原因而将非常大的方言连续区划分为不同的语言区,这种情况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都很普遍。欧洲的事例还包括这样一些连续区: 西罗曼语连续区,由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构成;斯堪的纳维亚语连续区,由挪威语、瑞典语和丹麦语构成;南斯拉夫语连续区,包括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和保加利亚语。在欧洲之外,人们还会提到这样一些民族语言,例如印地语和乌尔都语(Urdu)、泰国语和老挝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祖鲁语和科萨语(Xhosa)。所有这些变体通常被视作或被官方认作语言,这个事实归因于民族认同的标准语言的存在;这种标准语言可能更接近、但常常极为不同于很多讲话者认为的原初语言的语言变体(或方言)。 文字书写的重要性 尽管在非文字语言当中有时可以看到相当多的方言提升的现象(例如,这种提升始于人们普遍感到有必要模仿占优势的语言变体,比如政治上或文化上占优势的子群体、占统治地位的小群体或贸易和商业中心的语言变体),但狭义的语言标准化只能始于文字书写的采用。当然,可辨别的个体语言的形成和脱离大的方言连续区,常常发生在任何有目的的标准化干预之前;因此,当法国东北部的人开始用他们的本土话(而不是用拉丁语)在842年写作《斯特拉斯堡誓言》(该誓言将东法兰克和西法兰克统一起来)的时候,它标志着法语作为文字语言的开始,这就像所谓的《维罗纳之谜》(Riddle of Verona,一篇短文,或许是第一次验证了口语意大利语的存在,是9世纪的文本)标志着意大利语作为文字语言的开始。但大多数文字语言的早期阶段经常持续数个世纪,是以同时使用几个区域(有时是社会)语言变体为特征的。这样,文字英语的前现代阶段(尤其在中古英语时期)的文本是用北翁布里亚语、南翁布里亚语、莫西亚方言(Mercian)、肯特方言和其他语言变体写作的。今日我们熟知的标准(不列颠)英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以一系列事件为标志的,例如伦敦及其贵族政治的兴起、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赫里福德(Nicholas Hereford)在14世纪翻译的《圣经》(该文本建立了一种语言学标准,多被模仿,在接下来的很多时代被视作权威文本)、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词典(1755)中英语正字法的编纂以及其他重要事件。 在文学传统开始的时候,书吏和作家会尽力写下他们特有的方言,以一种当时存在的正字法标准为基础(例如,拉丁语的正字法标准被那些以罗曼语方言写作的作家采用)。统一标准的原因各异。例如,统治者或政府可能希望为其王国掌握统一的文字媒介,这将允许他们对行政事务进行中央集权的控制。在现代,宣传统一国家思想的希望可能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国家标准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被视作一个(或许新的)民族国家的象征。学者和学术团体也可能希望确定规则,他们考虑的是应该怎样生产文学,并常常以“古典”作家的用法为基础,这些古典作家被视作所有未来文学的模型,既是内容上的,也是审美形式上的。当然,较大国家范围内的地方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可能用语言和其标准化形式来宣传,以便获得一个区域群体的广泛接受,而这个区域群体的人掌握着分裂国家的力量。在一些情况下,跨越国界的标准语言获得认可,并被积极使用: 所有讲德语的国家都认可德国曼海姆的杜登(Duden)出版社编纂的词典确立的标准;在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国家,《古兰经》确立的古典阿拉伯语的形态学和句法(以及为了公共广播目的而确立的音韵学)模式,被所有公开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视作毋庸置疑的标准。只有在信奉基督教的马耳他,伊斯兰教不起作用,但马耳他的方言是各种阿拉伯语方言,这些方言采用土生土长的文字标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得到发展。 为了反映这些动机,语言标准化可能受到各种机构的推动,包括个人(例如于1492年创作西班牙语描绘性语法的作者安东尼奥·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自主社团(例如自1893年就活跃于爱尔兰的盖尔人同盟[Caelic League])、半官方性质的正式组织(例如1951年建立的挪威语委员会)或者官方政府团体(苏联针对混乱的官方区域语言进行的标准化活动就是这样的事例)。尤其对于后两个事例来说,正是由于政府有目的地指导国家或民族官方语言的标准化,词汇语言规划才被广泛使用。 正字法的改革 语言规划或语言标准化最普遍、最众所周知的事例是正字法的改革。它们可能是由简化现行正字法的激励促动的,因为人们感到现行正字法太复杂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字简化活动、1948年的丹麦正字法改革、1917年的俄罗斯正字法改革都是这样的事例)。另一种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治领域,希望使(有时非常人为地)一种语言不同于邻国所讲的密切相关的口语。有时一种不同的字母会被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一个恰当的事例就是“摩尔达维亚”语的字母。这是罗曼语的一个变体,从语言学上来说它与罗马尼亚的民族语言没什么差别,但在前摩尔多瓦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内却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之后,摩尔达维亚语不仅恢复了拉丁字母的使用,甚至放弃了摩尔达维亚语这个名称,改称罗马尼亚语)。塔吉克语的事例也与之类似。从语言学上看塔吉克语是波斯语的一个变体,用斯拉夫字母书写,而不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波斯语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因为当时塔吉克地区是苏联的一部分,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斯拉夫字母继续使用。最后,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情况值得一提。这两个语言主要因分别使用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而不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这两个变体之间的确存在语言学上的差异,但它们的界限并不是以天主教克罗地亚和正教塞尔维亚的文化边界为依据)。 然而,标准化活动并不局限于正字法,所有语言学分支都可能是语言规划活动的焦点。当标准化活动发生在语言的形态学和句法上的时候,采用高度人为标准的可能性自然是有限的,因为这些人为的标准在各种实际的口语语言中没有任何基础。这些标准可能以语言较古老的口语和文字语言变体为基础;它们可能是人为地作为文字标准保留下来,有时扩展某些用法超出了口语中实际使用的范围。因此,有人认为,某些过去时态的使用是古老语言保留在标准文字德语中的内容,而这些形式实际上在大多数口语变体中已经消失了。 专门词汇的不断改革 除了正字法需要改革外,标准语言的专门词汇也是语言标准化活动最经常针对的有争议的领域。这里可以列举出两个不同的倾向,作为最典型的倾向。第一个是,语言规划或标准化机构可能感到,一种语言使用大量从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借用来的外来因素(外来词)是不可接受的,应该用“本土”词语代替它们;这样的态度和活动通常被视作语言纯正主义。提供词汇的语言可能是之前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而政治独立以后,规划者可能试图减少这种语言的影响(拉脱维亚语中的俄罗斯因素和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语言就是这种情况);它也可能是一个相邻文化、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某些民族主义活动家敌视这种语言,或者成为种族仇恨的目标(这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反对法语因素的 世界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