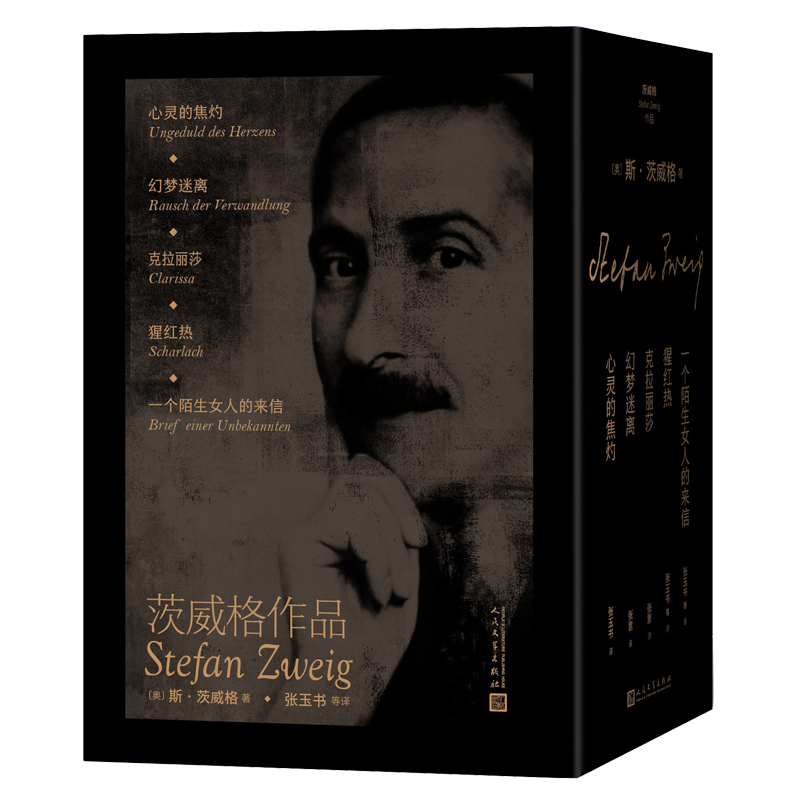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278.50
折扣价: 220.68
折扣购买: 茨威格作品5种套装
ISBN: 9787020159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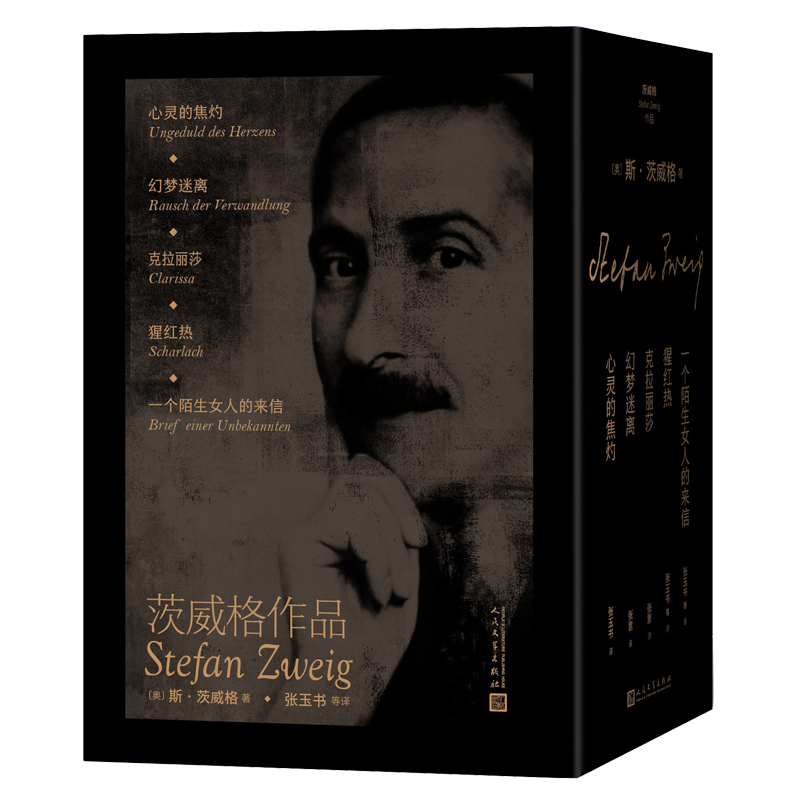
斯·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和平主义者。纳粹上台后,流亡英国、巴西。其小说以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见长。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旧书贩门德尔》《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巴尔扎克传》《良心反抗暴力——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约瑟夫·富歇》等。 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 译者简介: 张玉书(1934—2019),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译有海涅的诗歌和《勒格朗集》《论浪漫派》,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约瑟夫·富歇》《良心反抗暴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席勒的《强盗》《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奥尔良的姑娘》《图兰朵》《威廉·退尔》等。编有《海涅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小说全集》《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茨威格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张玉书先生的努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 本书其他译者章鹏高、赵登荣、胡其鼎、潘子立、张荣昌、张意等皆为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
克拉丽莎 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 克拉丽莎在日后的岁月里努力回忆她的一生,很难把她的一生连缀起来。就像大片的地面被黄沙覆盖,轮廓模糊不清,时间从上面掠过,像云彩一样飘浮不定,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明确的尺寸。好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她完全说不清楚,而有几个星期,甚至于几天,几小时却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情,还触动她的感情和她内在的目光。有时候她觉得,只有很小一部分时光,她是头脑清醒感觉清楚地度过的。另外一部分时光却是在身体疲惫,或者茫然尽职之时朦朦胧胧地打发过去的。 和大多数人不同,克拉丽莎对自己的童年时代知道得最少。由于特殊情况,她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没有一个熟悉的环境。她出生在加利西亚一座驻扎军队的小城。她的父亲,当年还只是参谋总部的一名上尉,被分配到这座小城。由于一系列客观情况不幸地交织在一起,使她的母亲不治身亡:团里的军医得了流感卧病在床,打电报召请邻近城市的医生前来诊治,医生却因大雪封路,来得太晚,未能治愈此时已转成肺炎的疾病。克拉丽莎在卫戍地受了洗礼,就和那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一起,立即被带到她祖母处收养。祖母自己也病病歪歪,要她照顾人,还不如让别人照顾她更好呢。祖母去世后,克拉丽莎就被托付给了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而她的哥哥则被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收养。他们居住的房子在变,那些伺候他们的用人的脸和模样也随之改变,时而是德国人,时而是波希米亚人、波兰人;从来没有时间让他们习惯环境,结交朋友,熟悉一切,适应一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的胆怯还没有克服,可是她父亲就在一九○二年,她八岁那年,奉命调到彼得堡去当武官;为了让这两个孩子生活更加稳定,家庭会议做出决定,把儿子送进军官学校,把克拉丽莎送进一座坐落在维也纳近郊的修道院学校去寄宿。克拉丽莎很少见到她的父亲,父亲的印象只有很少残存在她的记忆里,对于那些时日,她回忆起来,与其说是记得父亲的脸和他的声音,不如说是他那光彩夺目的蓝色军装,上面挂着叮当作响的圆形勋章。她很喜欢把玩这些勋章,可是她父亲严厉地把她小孩子的小手——她哥哥也受到这样的待遇——从这些象征荣誉的标记上挪开,为了对她进行教育。关于她的哥哥,她只记得她哥哥敞领的海员衫和他那平顺垂滑下来的金色长发,克拉丽莎为此还有点妒忌她哥哥呢。 克拉丽莎在修道院学校度过了她后来的十年光阴,从八岁一直待到她快满十八岁。同样,这么长的时间,只留下这么少的回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怪她父亲的一种性格特点。莱奥波特·弗朗茨·巴萨维尔·舒迈斯特在这段时间,稳步从上尉擢升为参谋总部中校这样的高级军衔,在比较高级的军人圈子里算是学识最渊博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之一。人们对他的勤奋好学、忠实可靠和远见卓识都表示出真诚的敬意,但是在这敬意之中也稍稍夹杂着一点嘲讽的意味;司令官在和比较亲近的军官谈话时,总是微微含笑地称舒迈斯特为“咱们的统计学家”,因为舒迈斯特干起活来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外表极为严厉,其实相当胆怯,并不灵活。他认为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信息中心乃是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他是慢慢地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在军事方面对全凭灵感、随机应变的行为一向持怀疑态度。他热心地收集外国军队能够正式公布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数据,作为剪报加以整理,不断补充,分门别类存进卷宗,谁也不得看上一眼。他的这种热忱使他得到邻国,德国参谋总部真诚的赞赏。就这样坐拥大量资料,他就变成了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在国外备受重视(事情总是这样)。不仅受人重视,甚至还为人惧怕,他的这座保存外国纸面上的军队和活生生的军队情况摘要的实验室,包括三四个房间;他经常不断地向奥地利驻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们发出调查表格,要求他们报告最最细枝末节的问题,供他充实他的军事标本夹。武官们为此对他百般诅咒。他起先是出于责任感和信念开始着手收集这些资料,渐渐地收集越来越多的细节并且把书面的和表格的汇总系统化,他对系统化的“酷爱”成为一种激情,甚至变成一种癖好。这种癖好填满了他因为早年丧妻形成的残缺不全、空洞荒芜的生活,使之获得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艺术家所熟悉的对于整洁和对称的小小的快乐,因为游戏的兴致是诱人的。他喜欢红色和绿色的墨水,削尖的铅笔。这具有古玩店的魅力。这一切他的儿子全然没有看见,这是父亲秘密的痛苦所在。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技术性的快乐,写些纸条,进行比较。先前他下班后,待在家里,穿上家居长袍,脱掉僵硬的领子,动作更加柔和,怀着感激的心情谛听他已故的妻子弹奏钢琴,让他有些僵硬的灵魂在乐声中松动一下;他们夫妻两人一起上剧院看戏,或者出去进行社交活动,这都使他散散心,放松一下。妻子去世以后,他不善于社交,夜晚一片空荡,毫无消遣,他便想方设法找事情做以此塞满空虚,用钢笔、剪刀、尺子在家里也设立一个个卡片,加以提炼,用来写成他公开发表的《军事战略表格》。在这本著作里自然不包括 关祖国利益的秘密材料。这样一来,通常在办公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情况,无须从隔壁房里取来。对于别人而言,最枯燥无味的东西,什么号码啦,数字啦,数量啦,差额啦,他都可以从中取得一种神秘的,对别人而言无法理解的认识,与其说他是军人,不如说他是个数学家;他越来越自豪地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用几万个这样个别的观察,为军队和帝国设立了一个武库,这是奥地利的宝库啊。事实上,在一九一四年,他对可以动员的师团做出的预计要比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的乐观估计正确得多。他越来越用书面文字取代口说的话语,越来越把他整理出来的材料替代客观世界。别人觉得他越来越严峻,城府越来越深,尽管他归根结底只是越来越孤独而已。他生活得越孤独,他就越习惯于用书面的记录来代替对话。每一种练习,只要不知疲倦地持续下去,持之以恒,就会出人意表地成为习惯,而习惯又会锻炼成约束和束缚:不再具有能力,只会系统化地从事某一件事情。 于是这个奇怪的士兵,要想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只知道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表格,即使通向他两个孩子的心灵,这个怯于表达柔情,又不善言辞的父亲也没有别的方法,只好要求他们经常向他书面报告自己生活和教育的进程,把这当作他们必要的责任。他刚从彼得堡回来,重新进入国防部之后第一次去看望女儿时,就给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带去一摞裁剪得一模一样的纸张,其中最上面的一张作为样式,他亲自清清楚楚地画好了线条,从此克拉丽莎得每天填写一张这样的画了表格的纸张,写明她每节课学了些什么东西、读了些什么书籍、练了哪些钢琴曲。每个星期天,她得把七张这样的纸,连同一封附信寄给父亲,这样她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以他的方式大大促进他的女儿成长,对女儿大有裨益,他就这样迫使女儿在童年时期就早早地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顽强的好胜心。事实上,这种报告的机械活动,每天记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使得克拉丽莎失去了这些年生活的概貌,因为这些印象非但收集不起来,无法形成整体,反而由于过早地向父亲报告,全都支离破碎,四下分散。克拉丽莎刚刚成熟,就自己决定不要立即终止这个怪癖,尽管她自己也感到,纯粹从空间来看,这种书面汇报是多么错误,这剥夺了她对许多事情的乐趣。她就像朵小花,过早被摘下揉碎。她日后思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父亲指示她一天天均衡地读什么,纯粹从空间而言,每天同样的分量,这就在学生时代剥夺掉她每一种对书籍和绘画的本能的欣喜。她后来自己认识到,欢欣鼓舞地阅读一小时,往往比一个月、一整年更能开启心智。修道院学校原本已经相当刻板而又单调,父亲的要求使得学校的生活更加难受。可是父亲过世之后,她在父亲书桌的抽屉里发现,她当年写下的那些关于自己度过的日日月月的纸张,都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心里涌起无以言状的深切感动。父亲把她寄来的报告按照它们原来的样子,一摞摞捆扎起来,整理得井井有条。父亲做事就是这样,绝不马虎,克拉丽莎可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对她非常满意,有些字句,父亲用红墨水在下面画了一道。有一次,克拉丽莎有句古老的诗句写不出来,父亲感到羞耻,简直难过极了。因为他很骄傲,于是他就拿起一把尺子,用尺子画去一个死去的快乐,画去一个死人。每个月他都把这些报告包扎成一包,一个学期就把好几包这样的报告都放进一个特别的纸箱里,里面还存放着她的成绩单,和院长嬷嬷关于她学习的进步和品行所写的一份报告。这个孤寂的男人晚上就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也经历一番女儿的生活。从院长嬷嬷写的那些回信,克拉丽莎可以看出,父亲怀着多少快乐——他自己从来不敢流露——以他拙劣的方式试图追随她的成长,为此他找不到别的工具,只找到一种工具,他自己使用的工具。克拉丽莎试着打开几页纸,这些纸什么也没告诉她,它们只是干巴巴地沙沙作响,而过去这可是活生生的生活,是对一些她早已遗忘的事情所做的功课。她试图回忆起事情究竟如何,对于这些早已不知去向的日子,她能够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少。 《幻梦迷离》 奥地利所有的乡村邮电所都相差无几:看看其中的一所就可知全部。这些邮电所都建造于弗朗茨·约瑟夫时期,使用同一资源,里面的设备同样寥寥无几或者简单划一,在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到憋屈,国库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就连坐落在冰川之中的最偏僻的蒂罗尔山区的邮电所,也都顽固地保持着那股老朽的奥地利行政机构的味道,一闻便知,这就是那冷丝丝的烟草味道和布满灰尘的卷宗霉味。所有邮电所的布局如出一辙:一道安装着玻璃板的木墙把房间按照严格规定的比例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对外开放场所,一个是办公区。在对外开放场所没有任何可以就座的地方以及任何其他舒适的设施,可见国家根本不关心它的国民是否会在这里逗留时间较长。公共区域唯一的家具一般就是颤颤巍巍靠墙放着的歪七扭八的斜面写字台,上面铺着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已经被无法数清的斑斑墨迹弄得黑乎乎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个嵌在桌子里的墨水瓶里看到的只是一团风干的墨糊糊,根本无法蘸着写字。就算桌上那个笔槽里凑巧有一支自来水笔,那它的笔尖肯定已经折断,根本写不了字。节俭的国库对于美观如同对于舒适一样的不上心:自从共和国把弗朗茨·约瑟夫的画像从墙上摘下来之后,拿来作为房间艺术装饰的充其量就是些海报,那些色彩特别扎眼的海报被贴在脏兮兮的石灰墙上,有的还在邀请人们去参观早已关张的展览,有些宣传购买彩票,在有些被人遗忘的邮电所里甚至还张贴着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的海报。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慷慨大方,充其量就显现在这些廉价的墙上装饰或许还有那个根本无人注意的“禁止吸烟”的告示上面。 相反,办公区域那边则让人格外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以最紧凑的方式象征性地展示了它不容忽视的权力和地域宽广。在那个被保护的角落放置着一个铁质钱柜,从窗户上安装的铁栏杆可以推测它那里时不时还真的收藏着数额可观的钱财。在工作台上闪闪发光的是一架莫尔斯发报机,上面的黄铜擦得锃亮,这可是个豪华玩意儿。旁边那部放在黑色镍制架上的电话机就显得朴素一些。这两个物件就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深受尊敬,因为它们只要接上铜丝就把这个偏远小村和辽阔无垠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其他邮政往来的家什就只好挤在一起了,包裹秤和装信的袋子,书籍,文件夹,本子,档案柜和那些圆形的发出叮当声响的邮资钱箱,秤和秤砣,黑色、蓝色、红色和紫色的铅笔,曲别针和夹子,绳子,火漆,海绵和吸墨器,胶水,刀子,剪刀和折纸器,所有这些邮政工作丰富多彩的小手工物件都玄乎地乱七八糟地堆在书桌那巴掌大的空间里。在许多抽屉和盒子里堆着各式各样的纸张和表格,满满当当的,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就这么近似挥霍地铺放着,但事实上这是假象,因为暗地里政府无情地清点着它那些廉价的办公用品中的每件东西,从用秃了的铅笔到撕碎的票券,从破成一缕一缕的吸墨纸到洗成小块的肥皂以及白铁洗手盆,从给办公空间照明的电灯泡到关门的铁质钥匙,国库都要求它的职员为每个用过的或者消耗掉的物件说明使用情况。铁炉旁边贴着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这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加盖了公章并带有无法辨认的签字。这份清单以算数的无情把相关邮政局哪怕最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企业物品的存在都标注出来。只要是这个清单上没有的物品就不能出现在办公空间,反过来,任何登记在册的东西必须都各就各位而且触手可及。国家机关就要求秩序和合法。 严格意义上讲,这份打字机打出的物品清单上也该登记上一个人,此人每天早上八点要拉起玻璃板,使用起那些原本毫无生命力的办公用品,打开邮政袋,给信件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具收据,给包裹过秤,用蓝色、红色和紫色的笔在纸上写出奇怪的秘密符号(密码),拿起电话的听筒,开动莫尔斯发报机的卷轴。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这个被公众大多称之为邮政助理或者邮政主管的人并没有被登记在清单上。他被登记在另一本公务册上,而这本册子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抽屉里,同样是一份名单,能够审核和监控。 在这个被国家鹰徽神圣化的办公大厅里从来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关于劳作和消亡的永恒法则,碰到国库的界限砸得粉碎,邮局周围的那些树木枝繁叶茂,然后又变成枯枝败叶,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终正寝,房屋坍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起来,国家机关就是用这种永恒的一成不变有意识地宣示着它的超凡权力。它范围内的任何一件物品如果用旧或消失,变样或衰败,领导部门就会定制并送来完全一样型号的另一件物品,以此给这变化多端的平凡世界一个国家优越性的典型例子。内容会消逝,但形式永远不变。墙上挂着一份挂历。每天都被撕下一页,一周七天,一个月三十天。等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挂历变得很薄,也已到头,于是人们要求一份新的,同样的版式,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印刷:又是新的一年,但还是同样的挂历。桌上有个带着一行行列表的账本,左边的那页要是写满了,数字就填在右边那页上,就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等到最后一张纸写满了,账本就记完了,那就再开始用另一个账本,同样的式样同样的版式,与以前的毫无区别。哪样东西要是不见了,第二天又会在那里出现,同等的样式,就像那个机构, 每个同样的木板台面上都一成不变地放着同样的东西,永远是同样形式的纸张和铅笔、别针和表格,再怎么换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国库空间里没有东西消失,没有东西补充进来,没有凋零和盛开,这里是同样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延续不变的死亡。在那丰富多彩的物品系列中唯一不同的是物品老化和更新的节奏,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以用一个星期,然后它就用完了,被一支新的同样的铅笔所替代。一本邮政账册可以用一个月,一个灯泡用三个月,一个挂历用一年。一把草编椅子的寿命是三年,然后会更换一把新的,而坐在这把椅子上消耗了整个一生的那个人的工龄是三十或者三十五年,然后一个新人就会坐上这把椅子。归根到底毫无区别。然后又变成枯枝败叶,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终正寝,房屋坍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起来,国家机关就是用这种永恒的一成不变有意识地宣示着它的超凡权力。它范围内的任何一件物品如果用旧或消失,变样或衰败,领导部门就会定制并送来完全一样型号的另一件物品,以此给这变化多端的平凡世界一个国家优越性的典型例子。内容会消逝,但形式永远不变。墙上挂着一份挂历。每天都被撕下一页,一周七天,一个月三十天。等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挂历变得很薄,也已到头,于是人们要求一份新的,同样的版式,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印刷:又是新的一年,但还是同样的挂历。桌上有个带着一行行列表的账本,左边的那页要是写满了,数字就填在右边那页上,就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等到最后一张纸写满了,账本就记完了,那就再开始用另一个账本,同样的式样同样的版式,与以前的毫无区别。哪样东西要是不见了,第二天又会在那里出现,同等的样式,就像那个机构, 每个同样的木板台面上都一成不变地放着同样的东西,永远是同样形式的纸张和铅笔、别针和表格,再怎么换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国库空间里没有东西消失,没有东西补充进来,没有凋零和盛开,这里是同样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延续不变的死亡。在那丰富多彩的物品系列中唯一不同的是物品老化和更新的节奏,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以用一个星期,然后它就用完了,被一支新的同样的铅笔所替代。一本邮政账册可以用一个月,一个灯泡用三个月,一个挂历用一年。一把草编椅子的寿命是三年,然后会更换一把新的,而坐在这把椅子上消耗了整个一生的那个人的工龄是三十或者三十五年,然后一个新人就会坐上这把椅子。归根到底毫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