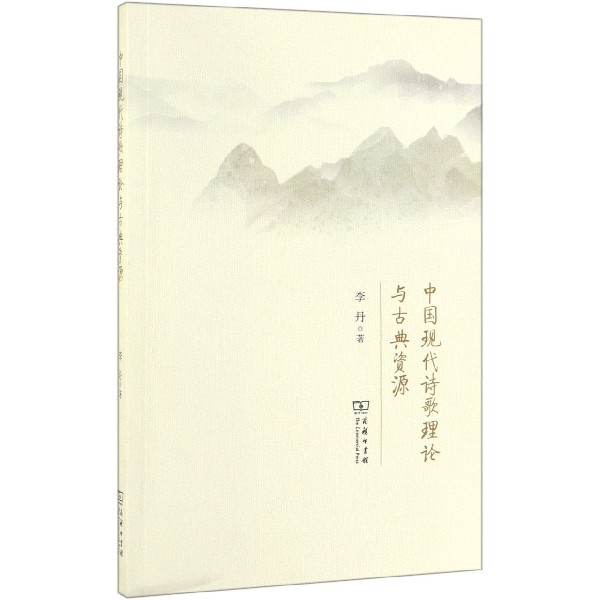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3.60
折扣购买: 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古典资源
ISBN: 9787100174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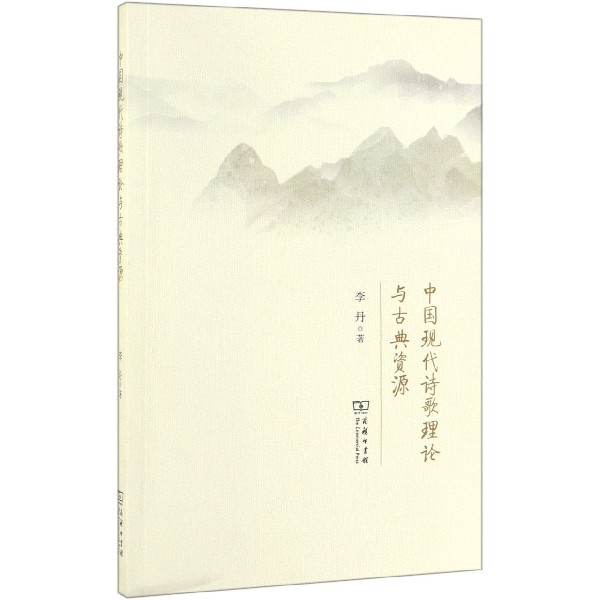
李丹,1968年生,陕西礼泉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导,上海师范大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负责人,女性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第五届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2008年上海市市级精品课程《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研读》合作者。已在《文学评论》、《学术月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一部《走向诗学》,参与编撰研究生教材《中国现代文论选》等。《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论文类二等奖。已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一项,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一项,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一项。主要从事新诗及诗论研究、文学批评研究。
胡适的“不用典”思想,不仅出现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还出现在此前的《致陈独秀》及此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其间跨度三年,尽管胡适白话入诗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是关于“不用典”的提法却发生了变化。在《致陈独秀》里,胡适认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其中“不用典”首当其冲,理由在于:“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意指套用古人诗词用语的写诗行为,与诗作这一包括语言创新在内的创造性活动相悖。由 于通信文体的限制,胡适于此仅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详尽地阐发了“不用典”观点。胡适区分了“广义用典”和“狭义用典”,所谓“广义用典”,“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故在诗作中可以保留。他还将广义的用典分为五种情况: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成语;引史事;引古人作比;引古人之语。并认为其中不乏成功的范例。所谓“狭义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关于“狭义用典”,胡适又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所谓拙者,“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他将拙典也分为五类,“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僻典使人不解;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用典而失其原意;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这是胡适根据当时诗坛的实际状况概括的。 由胡适对用典类型的划分及评判情形可知,“不用典”仅指狭义用典中的拙劣者,而广义用典以及狭义用典中的工巧者都受到他的认可。从份额上说,“不用典”与用典的比例是一比三,但胡适却用这1/3 部分的名称涵盖全部的内容,以局部命名整体,当是出于文学革命标语式宣传的需要。由此可知,胡适所谓的“不用典”,是指“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 的行为,即应摒弃的拙劣的用典。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彻底反对用典,他支持恰切地使用典故。也就是说,胡适的主张并不是对传统诗论用典观的反叛,而是与其一脉相承。 在中国古代诗论中,用典又称“用事”“使事”“隶事”,相关观点有以下五种。一是不主张用典。南朝梁钟嵘《诗品?序》称:“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注重诗人采用情景交融的语言,比如,“‘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认为清新刚健的诗歌,与诗人的观察力、想象力关系密切,而非对典故的倚重。二是认可适当的用典。随着诗歌题材的丰富和创作风格的多变,后代诗评家对用典的看法与钟嵘有所不同。旧题唐白居易《文苑诗格》称:“若古文用事,又伤浮艳;不用事又不精华。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也。”d 三是提出“用事无痕”的要求。元杨载《诗法家数》认为,用典贵“活”,“陈古讽今,因彼证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虽死事亦当活用”。清袁枚认为,“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知盐质”b。明清之际,王夫之《唐诗评选》评杜甫《琴台》诗云:“‘人间世’、‘日暮云’,用古入化。凡用事,用成语,用景语,不能尔者,无劳驱役。”“用事”入化,才能“即事为情,不为事使矣”。四是“诗贵用事”的观点。由于可以增加诗歌的历史文化含量,故应重视用典,清赵翼指出,“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五是对用典不当行为的批驳。反对用典中的“有意逞博,翻书抽帙,活剥生吞,搜新炫奇”;反对不管需要与否的一味使事用典,“假如作田家诗,只宜称情而言;乞灵古人,便乖本色”;反对“以故事填塞”,“填塞则词重而体不灵,气不逸,必俗物也”。 将胡适的观点与古代用典论相较,可见两者的异同。一是胡适认可的用典情形,与古代诗评家提出的活用、化用典故的观点相一致;二是胡适的“不用典”,指为典故所累而达不到增加诗歌美感反倒弄巧成拙的现象,也与古代诗论批驳的现象相同;三是胡适最为推重的“自铸新辞”“造词”“自己铸词造句”观点,与钟嵘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也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写真景物、真情感”的“不隔”说相衔接,即用新鲜饱满的语言,如实地描写自然人生,像“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并不需要依凭典故。重要的是,胡适与前人有所区别,他从诗歌语言革新的角度看待自铸新词问题。尽管古代诗论也涉及自铸新词的问题,却是在传统诗词语言模式内探讨,如黄庭坚谓:“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他在指出自铸新词比化用典故更难的同时,提出在传统规范内对前人词语加以改造。王国维的观点也没有脱离古典诗词的范围。胡适则身处新旧诗体转换之际,站在倡导者的高度,他所主张的自铸新词,其意不属于传统诗歌语言的范围,而且是为了突破古典诗词的格律规则,为了摆脱传统惯例的制约。这样,“不用典”的倡导直接指向文学革命所批判的虚伪、矫饰的贵族文学,对破除古典传统在创作中设置的种种束缚,破除束缚现代诗人手脚的清规戒律,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胡适提出的“不用典”与古代诗论关于用典的观点并不矛盾,他的主张,旨在促进文学革命。实际上,他的“不用典”特别指向以古人的艺术创造力代替自己的观察、审美和想象的过程,以古人的言辞代替自己的语言探索的写诗行为。对此,一年多以后,在另一篇文章里,胡适转换了阐述的角度。 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联互通关系?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生发的? 本书从诗歌语言论、文化论、审美论三个层面,层层剖析,庖丁解牛般论述了现代诗歌理论是如何从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厚宝库中汲取营养,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