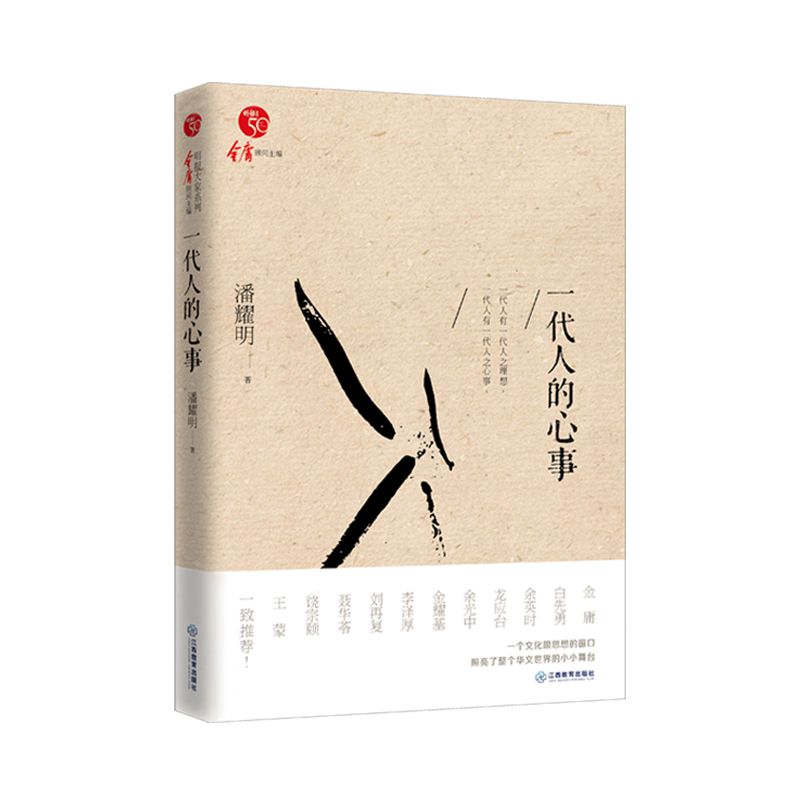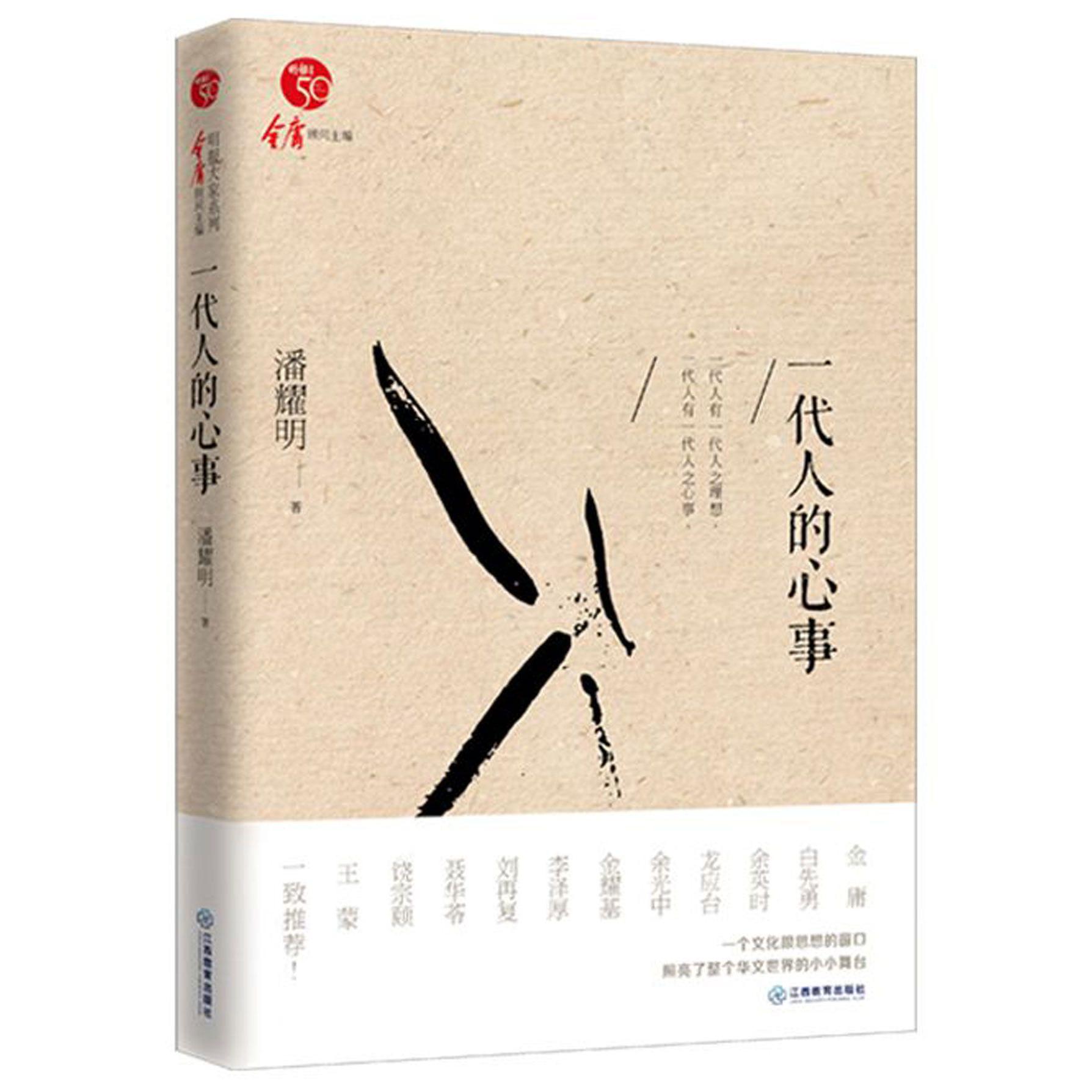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西教育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1.70
折扣购买: 一代人的心事
ISBN: 9787539290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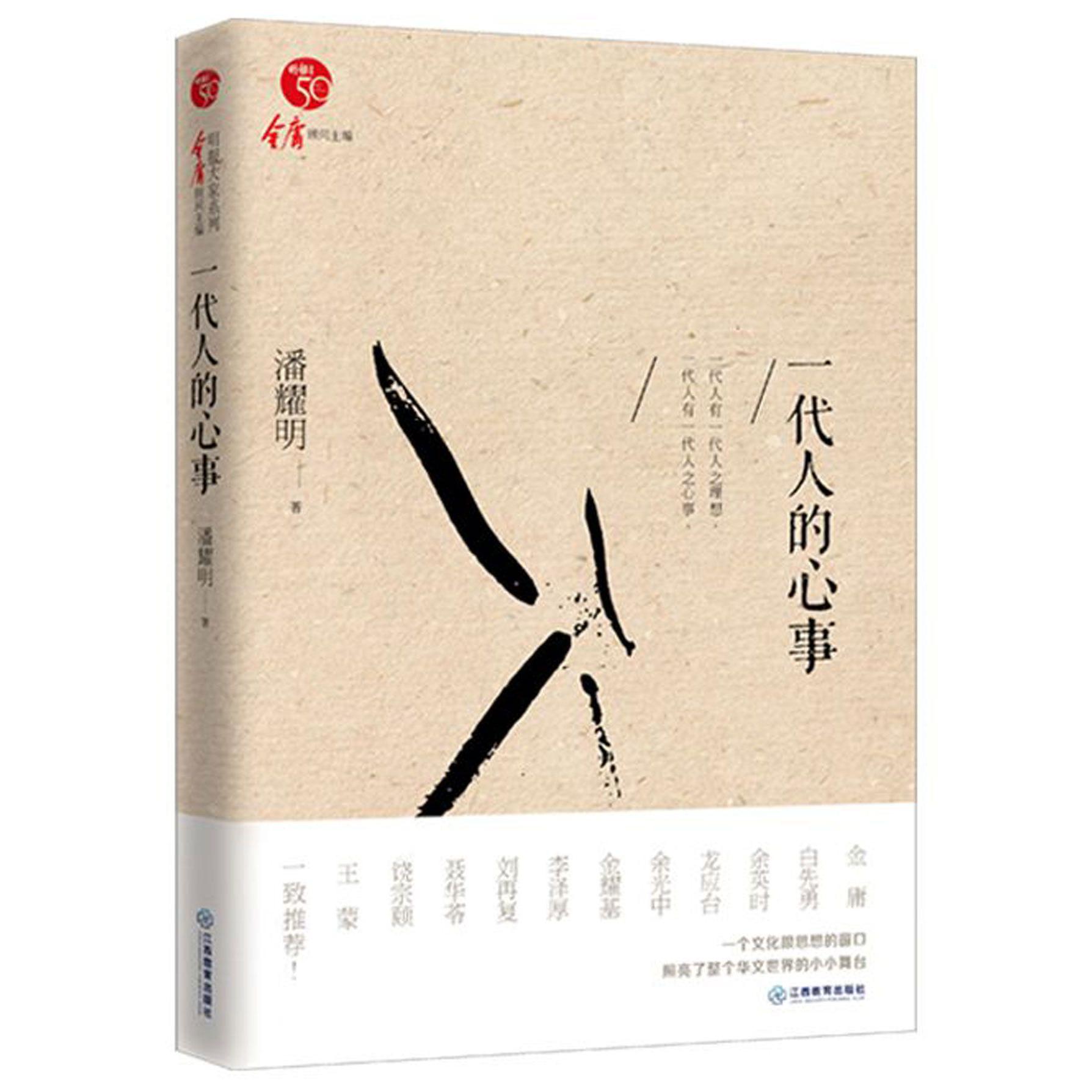
潘耀明,笔名彦火、艾火等,现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明报·字游》版主编、《明报·明艺》版主编。同时,还担任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等。 在内地、港台及海外出版评论、散文27种,其中《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被韩国圣心大学译成韩文并作为大学参考书,个别散文作品被收入香港中、小学教科书。2009年获日本圣教新闻社颁发的“圣教文化奖”。
春到人间万物鲜 “春到人间万物鲜”,是摘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长恨》句。 “人间万物鲜”的词意,别有一派生气、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时人所憧憬的前景。 新气象本来就不是无根的,它是脱胎于旧的窠臼,旧的渐去,新的油然衍生。 “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革》),在自然界,四季的形成,是因“天地革”(革:改革、变化)。在人类社会,何尝不如此?近三年来,因时局起了翻腾的变化,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 刚过去的猴年,时局如猕猴的性格,喧哗好闹,弄得人人忐忑不安,但社会经济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有了新发展,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诡异。总之,只要不是停滞不前,有革新,有变化,社会便会进步。 今年十二生肖属狗,狗的禀性,既有忠勇的一面,又有凶悍好斗的一面。狗在十二生肖中,是最具争议的。在汉语中,狗如神台猫屎,受到诅咒多过褒奖,几乎世间所有坏处,都一古脑儿往狗的身上扣,如狗官、狗口、狗命、狗腿子、狗爪牙……不一而足。连以爱心著称的冰心,一见到狗,也给吓得走不动(冰心:《山中杂记》)。 汉人这种心态,与乎中国少数民族和洋人对狗的亲昵,大相径庭!后者把狗揄扬为忠信护主、有情有义的良伴。中国的满族有一个“义犬救主”的传说,相传少年的努尔哈赤被明军追杀,行将被烧死之际,幸得随身狗伴沾水扑火。在西方人士眼中,狗又更是可以日夕相处的忠实侣伴。 若上溯自中国古代,狗非但不是不祥之物,反而被视为禳灾祛鬼的禽畜。古人称狗是“金畜”,春时所生,用以守门护府,可见,狗之被痛贬为千夫所指的恶物,是后来的事。首先见诸中国文人笔下的狗品、多如哈巴狗、丧家犬或鲁迅笔下的落水狗之流,人见人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正义之士、文化人被红卫兵当成狗头砸烂,还被踩上一脚!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有一篇狗的文章,描写人狗在暴风雨中互为依偎,患难中的温馨,倍添亲切感。换着中国文人,笔下的人狗相处,也许会被渲染成人狗对峙的怵怖气氛。 中国人对狗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来说,是陌生了,倒退了;少数民族、西方却是熟稔了、亲近了。文革把中国人对狗的仇恨,发挥到极致,以致人狗不分,可谓中国“狗文化”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有道是眼下中国大都市蔚为风气的养狗风,动辄以几万元、几十万元购一只狗为宠物,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狗文化”的提高?这种过犹不及的举措,旨在炫耀财富,相信也非人狗之福,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希望让人狗都得到改善,让人狗共生的世界回到中国。” 单是从国人对狗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水平,便使人对中国文化层次中的“狗意识”产生兴趣,本期“狗年文化”专题也许可以提供一点答案。名学者、“中国危机问题”研究专家何博传先生的《给狗看全相》,是他多年对狗观察、研究的心得。文章以丰富的知识,把中国人的“恨狗情意结”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带出国人的“狗忧患意识”,令人深省。 (原载1994年2月号《明报月刊》) 中国人的脸与西洋人的“兽性” 三十年代,日本有一位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脸及其他》,大意说初见中国人,让人感到较之西洋人和日本人脸上欠缺一点什么,但久而久之,看惯了也就没有什么,倒是后来反而觉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了点什么来着。后来发觉这多余的东西不是别的,却是“兽性”,从而得到这样的公式:人+兽性=西洋人。 这位日本作家在这里隐喻了中国人的温良恭俭让。相反地,西洋人及东洋人则野蛮了一点。从另一个意义来看,西洋人强横了一些,中国人柔顺了一点。 走笔至此,发生了美国的侦察机与中国战机碰撞事件,小布什政府表现得很是盛气凌人。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批准篡改侵略亚洲史实的中学课本,以期只手遮天,不难看出西洋人和东洋人“兽性”的一面。 至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在处理这起飞机碰撞事件和日本篡改历史的事件上,即使是西洋人“兽性”依然,中国人也再不三缄其口地谦让,终于发出有点硬朗的声音,尽管这声音的硬度和强度仍不如西洋人,但借以自慰的是,已远远超过鲁迅“无声的中国”年代了。 然而,回头一想,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性”始终不足以与西洋人的“兽性”相抗衡?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如果中国人脸上的“兽性”是后来才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 “家畜性”与“兽性”之不同,是前者已驯化了,为的是使牧人喜欢,便有了伪饰成分。所以鲁迅觉得倘不得已,不如带些“兽性”。 鲁迅生活的年代,中国贫穷落后,还在受着东洋人和西洋人的逼迫,知识分子更感同身受。鲁迅等人使用“兽性”“牧人”“家畜性”这类隐喻,寓意着压迫者、专制者及被奴化者的关系,别出心裁,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是,今天我们除了谴责兽性、调侃人性和家畜性,在处理世界各种冲突时仍要注重“理性”,依靠理性化解矛盾。中美的冲突自然也只有“理性”能够化解。中美关系再不是一般的国家关系,而是关系到“全局”的关键性的国家关系,这一关系的好坏,近则影响中国入世、海峡两岸局势、国计民生等大事,远则影响新世纪世界的前途,牵动着数不清的“大问题”。在“大问题”面前,当以“理性”解决为上策。为此,我们特别组织了“中美关系新危机大检视”专题,尽可能地分析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并带有具前瞻性的预测,供读者参考。 (原载2001年5月号《明报月刊》) 季先生“孤独的信念”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 自喻“孤独老人”的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潇洒地走了(他在无病痛中猝然而逝),为世人划出一道奇异的霞彩。 季先生自称“孤独”,因为在溷浊的世道中,他是一个清醒者。芸芸众生我独醒,其寂寞的心态可想而知。 季先生的寂寞感,带有沧桑的况味,也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和遭际:年少勤奋向学,青年负笈国外,研修学问,学成归来。老一辈知识分子像季先生一样,生于患难,长于濒临国破家亡边缘的时代,他们怀着一腔热血,以为可以学以致用,借以报国。曾几何时,欢欣鼓舞,迎来中国解放,却历经政治运动,被整治得死去活来;空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却要向工农兵学习,进行劳动改造,被迫改行干农活、粗活,浪掷光阴,斯人独憔悴。 季先生之孤独,因为他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文革”时北京大学生受江青指使,闹得天翻地覆,他不过说了一句戏语:“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季先生从此便被揪斗不止。 季先生事后回忆起在北大被批斗后游街示众,犹有余悸— 英雄们(编按:指红卫兵)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 与其他文化人一样,被批斗游街示众后,季先生便被关押在“牛棚”,为了那一句讽刺江青的话,被红卫兵诬蔑“与特务机构往来”,受尽凌辱和皮肉之痛。季先生没有倒下,因为他有一个信念:邪不能胜正。他写道:“在受批斗的时候,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季先生在“文革”和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中,却保持了清醒头脑和豁达,这就是“孤独的信念”所致。他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中仍坚持研究学问;在“文革”中,他历经磨难,仍偷偷翻译篇幅宏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季先生把他在文革的遭际和孤独的思考都深埋在心里,他盼望有一天把他的经历“和盘托出”,“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文革”过去,季先生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政治较宽松的年代。那是一九九二年,他以耄期之年,开始执笔撰写《牛棚杂忆》,六年后的一九九八年,才得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季先生有一段话很值得人深思: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 季先生写道:“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季先生认为许多在当年受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所以他呼吁受害者应写出来,“或者口述让别人写……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季先生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嫉恶如仇的笔致,由党校出版社予以出版,是否能陆续有来?按季先生的“孤独的信念”,应该是可期的,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曾指出:“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原载2009年8月号《明报月刊》) 运动记愧 杨绛以一百零五岁高龄走了。 认识杨绛有两个因缘。 第一个因缘,是我一九八一年春访问了钱钟书先生。因为这次访问,结识了杨绛女士。 此后每次去探访钱先生,都见到杨绛女士。杨绛女士兼具优雅丰度和娴淑的品格。她说话从来不亢不卑,不愠不火,语气轻缓、平和。正如她的处事方式:总是轻重有序,有条不紊的;说话也是柔声细气的,与钱先生谈笑文章,挥斥方遒,迥然不同。 钱先生是汪洋闳肆,文采风流,学问深不可测,恍如浩瀚大海。相反地,杨绛女士仿佛一条潺潺湲湲的小溪,澄澈明亮,文如其人,文章也是温文尔雅,干净利落,一清到底,没有半点渣滓。 从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可窥一斑。当年我任事的香港出版社,曾为她出版过英文版《干校六记》,也与她通过信。这也是认识她的第二个因缘。 在“文革”期间,不少文化人及干部被强迫下乡劳动改造。事后,许多人写了不少控诉文章,有血有泪。 杨绛则反其道而行之。她只是如实记录干校劳改的生活细节、艰苦、劳累,也不乏表露人性真情的一面,哪怕微弱的闪光。难得的是,她没有放进自己的情绪或做任何个人意见。 杨绛的《干校六记》,口碑极好,一纸风行。 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短文中幽了太太一默。他觉得《干校六记》漏了一记。钱先生为漏了这一记,立了题目名:《运动记愧》。 钱先生表示,关于“干校”(劳动改造),“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 笔锋一转,钱先生矛头直指那些批斗知识分子凶巴巴的群众。 他指出:“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在那极端的社会,对运动采取“不很积极参加”,正是良知未泯,甚至是颇有点胆识的人。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钱钟书)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前者没有救赎的心态,缺乏反省的自觉性。凡是自己犯错的,仿佛都有借口推搪得一干二净。换言之,一个人犯错不在于一己的责任,倒要找到导致自己犯错的一千个理由,尽显柏杨笔下丑陋的国民性。 钱先生这篇《小引》,意在说明,杨绛《干校六记》对造反派的哀而不怨,不尽苟同,反而进而指出人性卑劣的一面,可以警醒后来者。 中国毕竟太缺少“记愧”的人,更谈不上气节! (原载2016年7月号《明报月刊》) 1.它是一个文化跟思想的窗口,照亮了整个华文世界的小小舞台. 2.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理想,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心事。 3.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有三大里程碑,即《新民丛报》《新青年》与《观察》,第四个里程碑则非《明报月刊》莫属,以持久的影响力而言,《明月》更是后来居上。兹值《明月》五十周年纪念,我谨从读者的立场,向《明月》创始人和历届编辑人士致最高的敬意。——余英时 4.《明报月刊》自创办之日起就致力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一贯坚持恪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创刊50年来,《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华人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潘耀明 5.陈寅恪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要具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明月》五十年来之所以有出色成绩,即是因《明月》主事诸君子是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自勉自励的。——金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