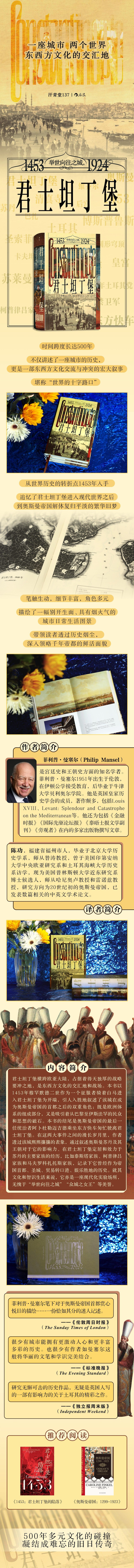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79.40
折扣购买: 汗青堂137·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
ISBN: 9787513946049

作者 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是宫廷史和王朝史方面的知名学者。菲利普·曼塞尔1951年出生于伦敦,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后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他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成员,著作颇多,包括Louis XVIII、Levant: Splendour and Catastrophe on the Mediterranean等。他还为包括《金融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旁观者》在内的多家出版物撰写文章。 译者 陈功,福建省福州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昝涛教授,曾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和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系访学,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师从哈尼奥卢教授和雷诺兹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已发表数篇相关的中英文学术论文。
14 青年土耳其党人 我们需要一个先进和现代化的土耳其。那时,君士坦丁堡将会是光源,穆斯林将会前来,在这里不带偏见地学习科学和文明的理念。 ——阿卜杜拉·杰夫代特,1908年8月20日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的君士坦丁堡一度为“幸福门”的名号正名。一些行省城市还在抱憾苏丹专制主义的结束:在首都,民众则长期以来受到青年土耳其党宣传的润泽,他们在大街上互相拥抱。谢里夫阿里·海达尔挤在狂喜的人群中,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只有那些经历过压迫和奴役岁月的人才能体会这一切”。苏丹近侍的女儿、不久之后的女权主义者和作家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起穿过加拉塔桥的人浪“发散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人们情绪激烈,喜极而泣,以至于人类的缺陷和丑陋在那一刻完全被抹去”。这座城市找到了新的角色。它既是帝国的首都,也是革命的总部。1 苏丹迅速地恢复了宪法,他因此树立起了从邪恶的近臣手中解脱出来的慈父人设。7月26日,6万人聚集在耶尔德兹宫门口。他们扛着用法语和奥斯曼语书写的“自由、平等、友爱、公正”旗帜,佩戴着红色和白色(奥斯曼国旗的颜色)的“自由帽章”,这是为了模仿1789年巴黎的三色帽章。当苏丹在阳台上现身时,欢呼声“我们的帕迪沙万岁”响起。他回复道:“从我继位以来,我就全心投入到祖国的幸福与拯救的事业之中。我的伟大设想是臣民的幸福与获救,对我而言,臣民和我的孩子没有区别。真主为证!”更多的欢呼声随之响起。多年后,苏丹的画师福斯托·佐纳罗写道:“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没有听到这样的呼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欢腾的人民。”明信片上,太阳在君士坦丁堡的圆形穹顶和宣礼塔上冉冉升起,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法语和奥斯曼语的“自由、平等、友爱”标语的上方微笑,这象征着一种信念:革命是君士坦丁堡的新黎明。2 在新的大维齐尔,即精明而勤奋的卡米勒帕夏的领导下,耶尔德兹宫减少了一部分奢侈排场和大部分权力。苏丹的间谍像太阳下的雪一样消失了。副官、园丁和阿尔图罗·斯特拉沃罗的歌剧团都被解散了。费希姆帕夏被私刑处死。新一批君士坦丁堡流亡者抵达开罗:像伊泽特帕夏这样的前任大维齐尔和各部大臣替代了1908年之前避居此地的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当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和军官得胜回到首都时,似乎整个帝国的人都在加拉塔桥和码头夹道迎接他们。 对于一个在30年专制主义统治后突然迎来自由的首都而言,君士坦丁堡的氛围似乎格外平静。然而,真正的权力不在卡米勒帕夏领导的文职政府手中,而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由三位爱国者领导,他们将会在未来十年主宰政府:恩维尔帕夏、杰马尔帕夏和塔拉特帕夏。恩维尔是一名理想主义的青年军官,他相信自己是国民偶像,有能力实现民族的梦想;杰马尔是一名精力充沛的进步主义官员;塔拉特是健壮的前萨洛尼卡邮政官员,是三人中最无情者,尽管脸上总带着甜美的微笑。该委员会成员故意留在幕后,但每周都拜访大维齐尔和大臣,以通告他们委员会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下达指示。宫廷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秩序。苏丹并没有等待“惯例的翻译”,而是“直接大笑着”告诉奥地利大使帕拉维奇尼侯爵(因其经常预知厄运而被称为“佩拉的卡桑德拉”),他无意撤回宪法,“五年里不会,十年里不会,就算十五年里也不会撤回”。3 同年秋天,人们通过盛大的自由、友爱和鲜花仪式庆祝选举的进行。投票站设立在清真寺、教堂和警察局的庭院里,装饰有菊花、玉兰花和月桂。11月25日,点缀着花朵的投票箱在瓢泼大雨中被人们用皇家带篷四轮马车送进“高门”,仿佛是凯旋的战利品一般。票箱队伍由骑兵队和鼓乐队领头,四轮马车护送,马车上坐满了身穿亮色衣服、高唱爱国歌曲的学童,后面跟着步行的民众,他们也唱着歌,手中挥舞着红色的奥斯曼国旗和绿色的伊斯兰教旗帜。4 这座城市庆祝宗教间的友爱,以及自由选举。7月,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参加了在塔克西姆和巴鲁克利的亚美尼亚公墓里为1895年和1896年屠杀受害者举行的安魂弥撒。萨巴赫丁前往法纳尔,再次向大牧首保证新政权将会维持希腊人的特权,他称土耳其国内的希腊要素是秩序和进步不可缺少的部分。12月,库尔德人、拉兹人、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和阿拉伯人穿着民族服饰、带着武器,护送最后一个投票箱经过加拉塔桥,他们的服饰与身边穿着统一制服的奥斯曼官员、毛拉、教士和拉比形成对比,但欢乐之情是共有的。选举前发生了一场争议,因为有一些希腊投票者无法证明自己的奥斯曼公民身份:这些人此前选择希腊王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部分是为了避税而为之。于是,一群愤怒的希腊人从佩拉出发,经过加拉塔桥游行到“高门”,要求从卡米勒帕夏处得到一份书面保证,确保他们的投诉得到调查。然而,在照片中,毛拉、希腊司铎和亚美尼亚教士与拉比并肩共同庆祝选举成功举行,奥斯曼军人则围拢在他们身边。在1908年选举的代表中,有142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5名阿尔巴尼亚人、23名希腊人、12名亚美尼亚人(包括4名亚革联成员和2名钟声党成员)、5名犹太人、4名保加利亚人、3名塞尔维亚人、1名瓦拉几亚人。“青年土耳其党”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者使用的通俗称呼,“青年土耳其党”大约有60名代表。其他人之中有反对世俗化的乌莱玛、保守派,以及支持去中心化的自由主义者。5 12月17日,议会开幕,它并没有像1877年那样在皇宫召开,而是在圣索菲亚清真寺旁边的议会大楼里。兴奋的人群涌入周边地区。男男女女攀上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屋顶放飞鸽子和海鸥,他们渴望看到下方的庆典。大教长出现时欢呼声更加响亮了,他是宪法的著名支持者,也是最受欢迎的代表。突然,乐队从演奏新谱写的《宪法进行曲》改为演奏《哈米德进行曲》,这首曲子也在耶尔德兹宫的周五聚礼上演奏过。两个小时后,苏丹在枪骑卫兵的护送下到场。他驼着背,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他不是踏步走上俯视代表们的讲台,而是拖着脚上去的。苏丹医生之子,即议会上院议员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耶尼写道:“他看起来像是被敌人追逐的败军之将,几乎如一具行尸走肉,当他的嘴唇张合时,他发出的声音小得都无法让自己听见。”首席秘书大声朗读他的讲稿,演讲稿中苏丹假意提到由于民众的教育水平最终让选举成为可能,便出于自己的意愿召唤民众前来。那一夜,清真寺、宫殿、内阁各部、水滨别墅和船只都灯火通明,这是对新时代的庆祝。6 此时,苏丹还不是强弩之末。12月31日,受邀在耶尔德兹宫中用晚餐的代表—位于大间阁的主厅—在宫墙内显得谦卑而充满敬意。他们根据传统的要求亲吻苏丹的手和外衣袖子,而不是像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偏好的那样只是深鞠一躬。苏丹的首席秘书保证苏丹将与人民同在。苏丹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7 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声望遭遇了打击,部分是因为所谓的“古埃索夫事件”。苏丹总是提防国内民众和外国人之间的联系,不鼓励举办外交晚宴。外交大臣陶菲克帕夏是一名和蔼的老人,以临危不乱闻名,9月14日,他在自己位于德国使馆边上的宅邸设宴招待外交官。保加利亚外交代表M.古埃索夫没有受到邀请,这表示奥斯曼帝国政府依然把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视为奥斯曼行省长官,而非独立君主。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权威姿态使大公勃然大怒,于是他在10月5日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保加利亚沙皇。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外交日程都因此被打乱了。奥地利随之宣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同样在理论上是奥斯曼的行省),这赶在了奥地利外交大臣与俄国外交大臣协定的日程安排之前,而俄国外交大臣原本同意从奥斯曼帝国得到向俄国战舰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许可作为补偿。俄国受到了羞辱。奥地利—俄国关系恶化,加快了欧洲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步伐。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两个附庸行省(在同年还失去了第三个,即克里特)。君士坦丁堡的爱国商人掀起了对奥地利商品和船只的抵制。奥地利商船无法在加拉塔的码头卸货。只有在奥地利政府向奥斯曼帝国当局支付一笔为数不小的赔偿后,这场抵制活动才结束。8 在“解放、平等、自由和公正”革命的同时,君士坦丁堡经历了一场类似现代极端主义的运动。一个叫“盲人阿里”的传道者在法提赫清真寺里贬责宪法。1908年10月7日,他领导了一大群把斋群众去耶尔德兹宫见苏丹,苏丹在窗口现身。“盲人阿里”向他呼吁:“我们需要一位牧羊人!没有牧羊人,羊群无法生存!”极端主义者要求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查封酒馆、剧院,禁止摄影,以及终结穆斯林女性在城中公开行走的自由。他们的信仰体系是清教徒式的,和17世纪的伊斯兰教狂热派别卡迪扎德派类似。这体现出城中的伊斯兰生活有了自己的势头,独立于革命和宪法。之后,“盲人阿里”被逮捕入狱。 宗教极端主义者并不是孤军奋战。反对派的不满情绪影响到许多驻扎在城中的军人,即使是从萨洛尼卡调到君士坦丁堡以加强新秩序的革命军,也是如此。他们之中不仅有为极端主义所吸引的虔诚穆斯林,也有因特权被削减而愤怒的保皇派。之前用来做礼拜的时间现在被分配给军事操练。之前由苏丹晋升的军官现在被支持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军校毕业生取代。习惯于耶尔德兹宫闲适生活的卫兵因为可能会被派到希贾兹服役而发动哗变。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面临失去传统的免税权和免于兵役的自由。9 宗教极端主义报纸《火山报》(Volkan)于11月创刊,其计划是“在哈里发国的首都传播神圣团结的光芒”。这份报纸歌颂苏丹的虔诚和慈善,指责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忘记了“君士坦丁堡不是巴黎”。1908年夏天的和谐氛围消失了。卡米勒帕夏希望军队去政治化,更加亲近宫廷,2月9日,他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压力下辞职。1909年4月3日,穆罕默德协会成立,该协会在圣索菲亚清真寺召开会议,宣布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为敌:“前进!如果我们注定要以殉难者的身份倒下,就不要撤退!”许多苏菲派人士和伊玛目支持它;高级别乌莱玛继续忠于宪法。10 4月7日,一份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报纸的编辑在加拉塔桥上被杀,加拉塔桥是一个绝妙的谋杀地点,因为凶手可以轻易地消失在人群里。4月12—13日晚,军人和士官发动哗变,高喊:“我们要伊斯兰教法!”他们逼退了长官,游行到圣索菲亚清真寺边上的议会大楼。他们的要求是:实行伊斯兰教法,开除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一系的大臣和军官,将穆斯林女性限制在家中。当他们对议会大楼发起进攻时,苏丹迅速接受了他们的方案。他派出自己的首席秘书,向在议事厅及其周边逡巡的战士和霍贾(穆斯林导师)宣读公告。根据其首席秘书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发生了如下对话: 请回到你们的兵营里,放轻松,孩子们,苏丹原谅你们。 告诉那位老人,新来的小子正在排挤我们,亵渎我们的宗教,诋毁苏丹。 陶菲克帕夏随之就任大维齐尔。苏丹并没有煽动兵变,但是适时地对这次哗变有所预见,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利用。他重新取得了对关键的陆海军部门的控制。一些议会议员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开会,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逃进了圣斯特凡诺游艇俱乐部,那里靠近1878年俄国军队的扎营地。军队洗劫了《共鸣报》(Tanin)等支持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报刊高层,杀死了司法大臣和一些司法官员。这一事件既展现出革命者对民众和军队感受的无知,也体现了君士坦丁堡的王朝保守主义之顽固。它比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军队更忠于君主,后两者近来(分别于1905年和1906年)支持革命。11 在第一波血洗之后,军队重整纪律。但是,萨洛尼卡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拒绝接受新政府的权威。他们的文字中体现出极其反对首都的情感。阿卜杜勒哈米德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和伊斯兰教、奥斯曼家族,以及两圣城的监护权一起视为帝国的四根支柱。青年土耳其党人谴责“在旧拜占庭的可悲环境中编排的阴谋”,决心“净化”首都。12 一支叫作“行动军”的队伍在马哈茂德·谢夫科特帕夏的带领下从萨洛尼卡行军到首都,马哈茂德·谢夫科特帕夏是一名阿拉伯裔的青年土耳其党将领,是德国战术和法国文学的崇拜者[1879年,他翻译的法国小说《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一时间,城中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即使是加拉塔桥,也是如此。苏丹的政府可能本来期待着兵不血刃地收回权力,因此没有作战的欲望。苏丹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没有得到精英的认可。乌莱玛说服大部分兵变者放弃抵抗,发布宣言,声称伊斯兰教法不是与专制主义相兼容,而是与宪法相容。苏丹从谢夫科特那里得到消息,谢夫科特再次保证他并不计划废黜苏丹,苏丹拒绝了忠诚于他的军官的建议,没有下令抵抗。 在4月23日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最后一次周五聚礼上,军队和观众的热情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苏丹也头一次满面笑容,亲切地接见大家:为了这个场合,他的脸颊涂上胭脂,胡子也染了色。伊玛目劝诫穆斯林相信哈里发,这是改革的前兆,也是紧急动员的信号。一些旁观者感到他将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但是他从四轮马车向外看去,没有在梯形外交看台上找到外国大使:欧洲站在注定是胜利者的那一边。13 1.时间跨度长达500年,不仅讲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更是一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宏大叙事,堪称“世界的十字路口”。 2.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453年入手,追忆了君士坦丁堡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到奥斯曼帝国解体复归平淡的繁华旧梦。 3.笔触生动,细节丰富,角色多元,描绘了一幅别开生面、具有烟火气的城市日常生活图景,带领读者透过历史烟尘,深入领略千年帝都的鲜活面貌。 4.联系当今严峻的国际形势,该城作为世界的枢纽,将继续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些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