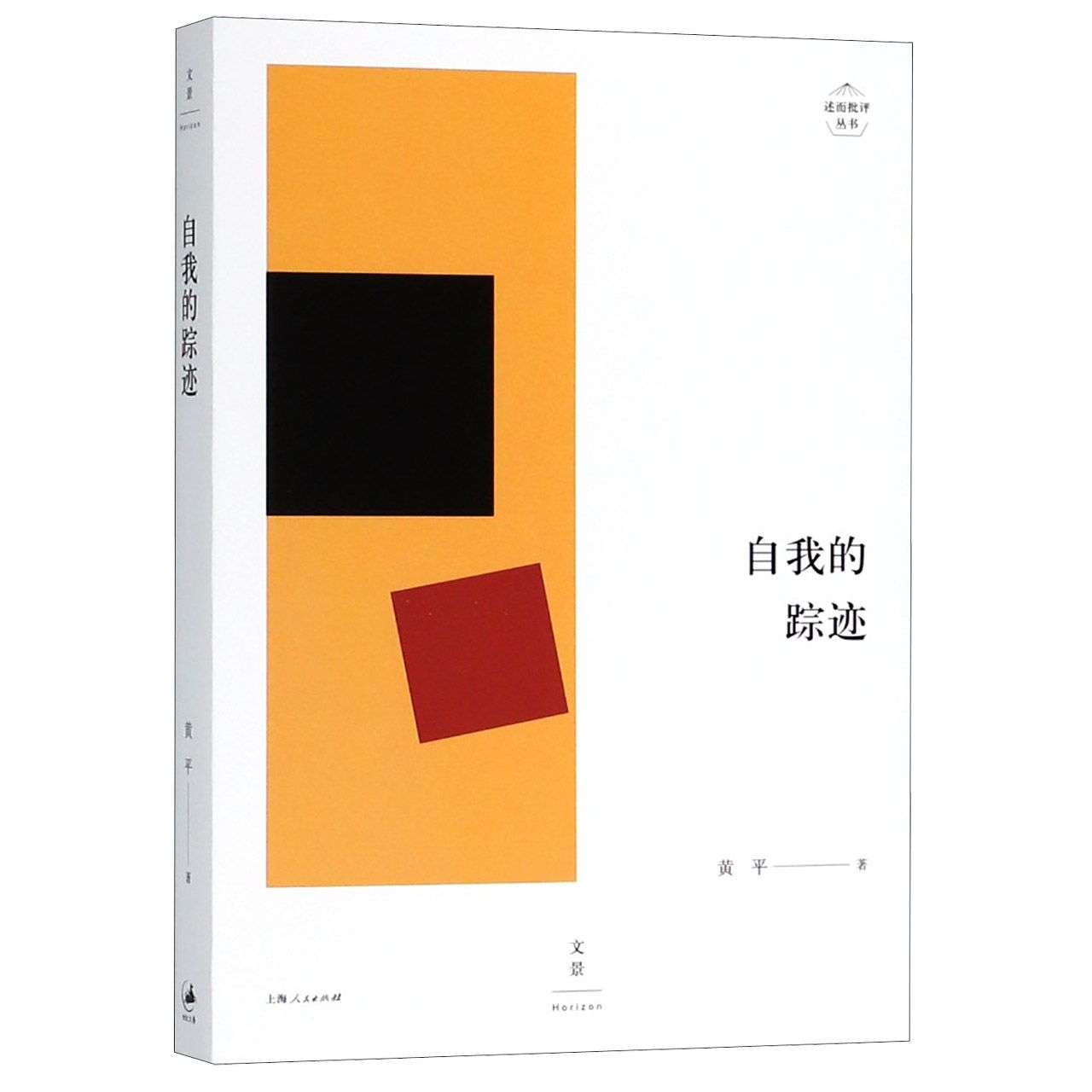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2.40
折扣购买: 自我的踪迹/述而批评丛书
ISBN: 978720815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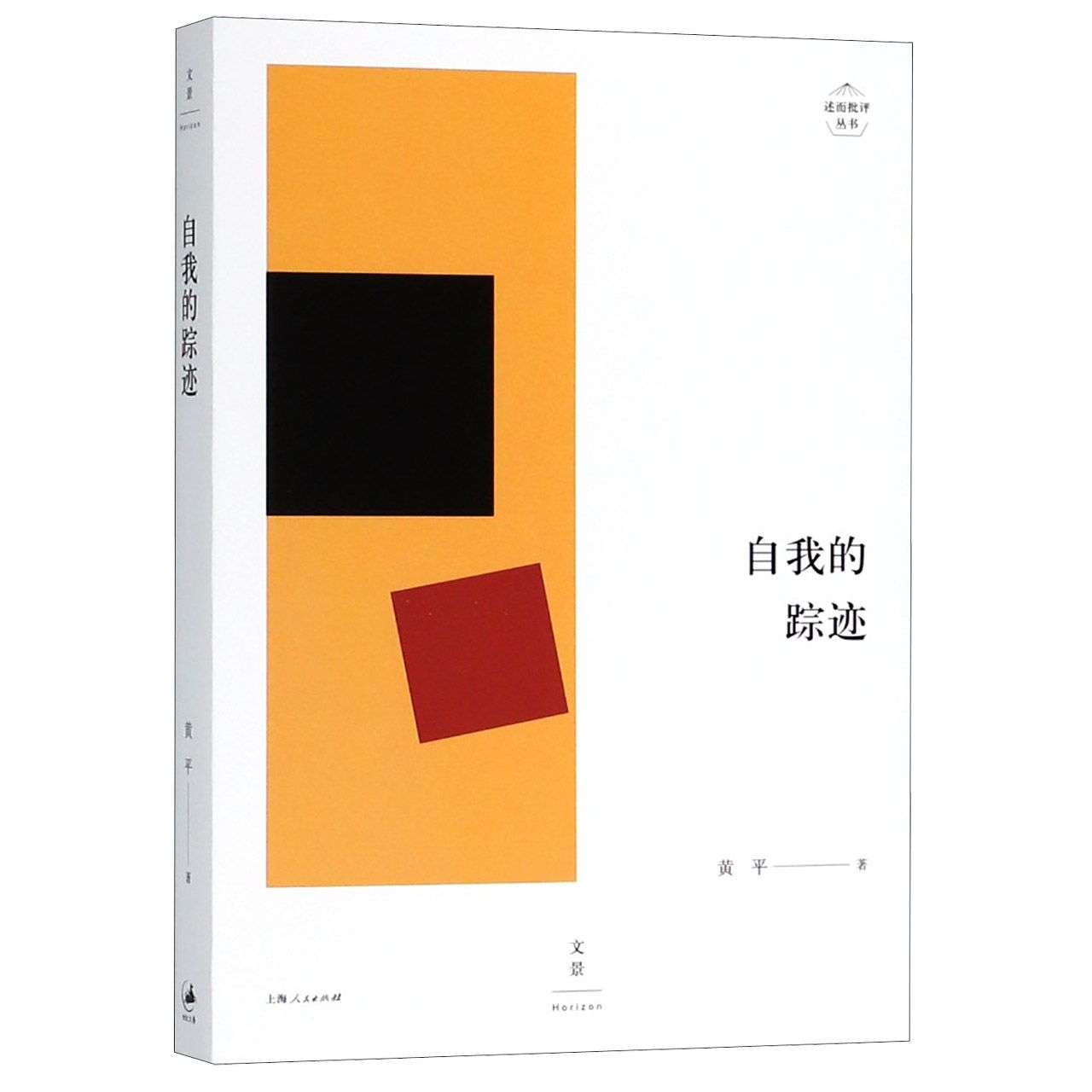
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与“母亲”的对话,更表 现为“我”通过对于母亲的“回忆”来完成自我认识 与自我教育。如同李建立的梳理:“讲述母亲的故事 之前,‘我’是一个面对人生困惑的青年,总想辩驳 而又不断退让;讲故事中,‘我’一直是一个不解世 事的儿童,说话幼稚,仅仅对成人世界有着好奇,却 无法解释;讲故事后,‘我’成了一个可以告知别人 如何行事的人,开始大声辩驳,滔滔独白。”“我” 之所以经由“叙述”获得“成长”,对于外部世界有 所指教,正在于通过“爱”确证了“自我”的合法性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不仅仅是两性 之爱,而是一处意义的空间,标识出“自我”的内在 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内在性”的一面得以显露 ,“外在性”的一面显得虚弱而不真实。对于叙述人 “我”而言,“内在性”的“爱”远比外在的“法律 ”与“道义”更为牢固与坚实。“内在自我”成为一 种更高的人性向度。经由“内/外”的辩证剥离—— 首先剥离出身体,其次剥离出社会关系——“自我” 不断向深处下潜,最终“自我”的内在性成为独立的 对象。诚如查尔斯·泰勒的分析:“这种第一人称的 自我转向,对于我们通向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因 为事实上这是我们通向上帝的一步——这对于我们理 解道德的根源开创了新的理解,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化 正是建基于此。” 既然通往天国的道路要通过内在的自我,“意义 ”的等级秩序由此得到重写。在小说中原来维持老干 部与妻子的“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 ”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爱”,“爱”只是和“自我” 的“内在性”相关。这样的“自我”跨越一切束缚, 最终走向天国,母亲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在 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 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 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西方式的、现代式的“自 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终于历史性地出现。《爱, 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 后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说,比如当下泛滥开 来的小资文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张洁。当时的批 评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就隐隐约约地感 觉到这一点。李陀有一段分析今天看来很有见地:“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里,作家把对人物 内心生活的表现上升为首位的、主导的东西,小说的 其他艺术要素,都降为从属的东西。因此,小说表现 和描绘的一切,都带有叙述者兼主人公之一的‘我’ 的主观感情色彩;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回忆、议 论都不再是传统小说写法中的客观描写和叙述,而是 ‘我’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张洁来说,她之所以在1979年写出这样一篇 小说,除了以她所热爱的契诃夫小说为代表的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