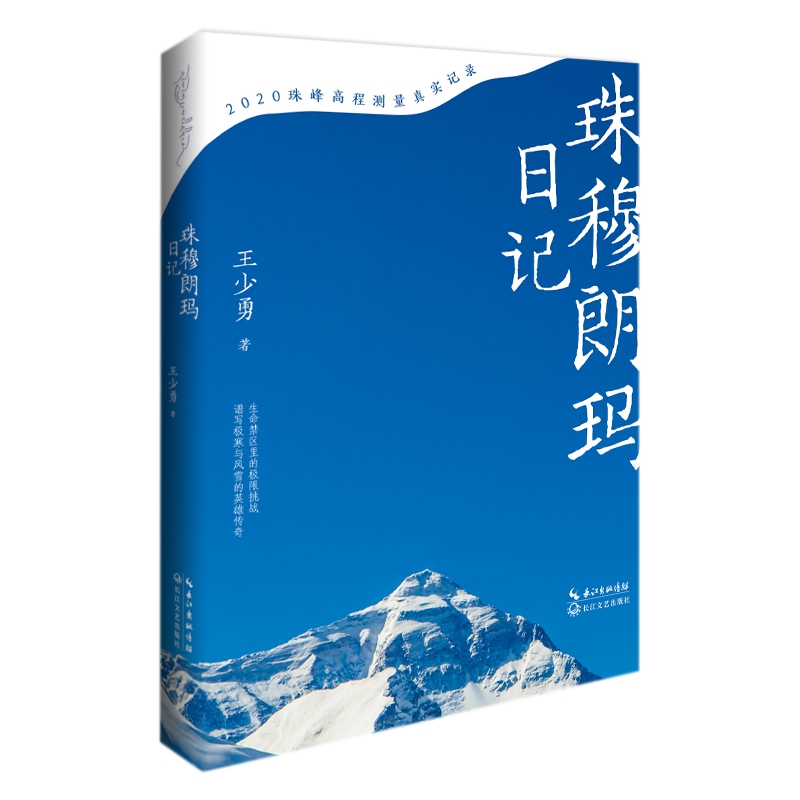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90
折扣购买: 珠穆朗玛日记
ISBN: 9787570217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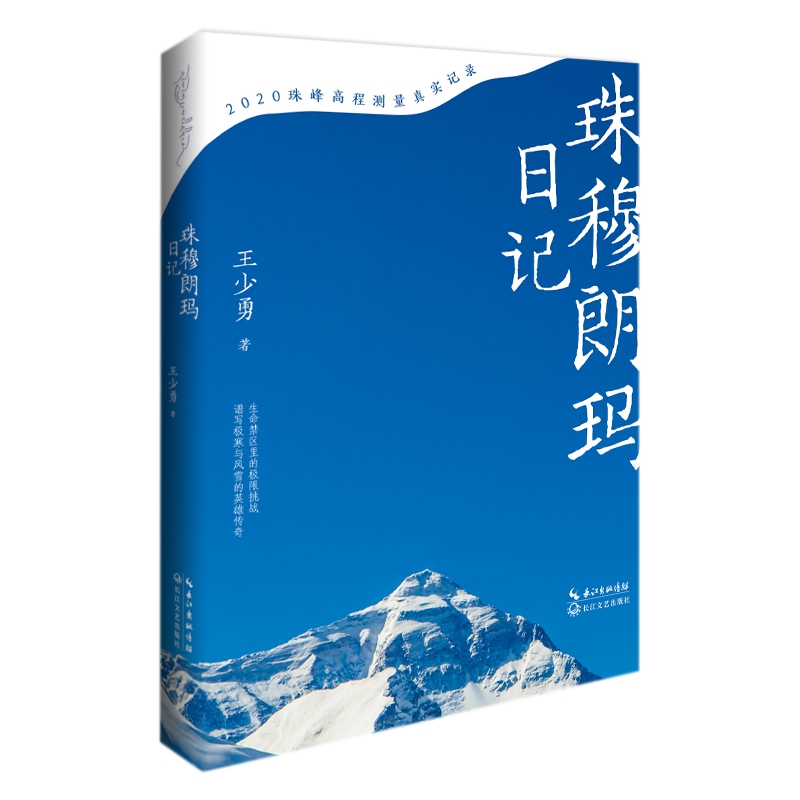
王少勇,诗人,二十世纪末生长于鲁西南,后移居北京,执行过中国大洋科考、抗震救灾等报道任务,作品收入多种选本,现为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首席记者。
4月15日 定日 多云转晴 停电了,不知是白坝村停电,还是整个协格尔镇都停电了。当地人说,这很正常,一年至少有60天会停电。没有电热风,没有电褥子,这将是个黑暗而寒冷的夜晚。 下午,在酒店外面看到测绘队员正在测试GNSS设备,我们便过去拍摄,并采访了其中的一位。他50岁上下,个子高高的,口音很重,说话很朴实,笑起来甚至有些腼腆。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我叫张建华。张建华!2014年全国感动测绘人物。我一下记起来了。我说,我写过您,您是不是去非洲执行过任务?是不是参加了上次珠峰测量?2015年我去国测一大队采访,回来写了一篇5万字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段就是写他。当时我并没有采访到他本人,而是根据他的事迹材料和别人的讲述写的。这次珠峰高程测量,他担任技术质量现场负责。他说年纪大了,这次上来血压一直高,常常头晕。前几天翻越加吾拉山口时,他的两只手发麻,随即肿了起来,停车休息了许久才缓过来。 15年前珠峰高程复测,35岁的张建华是交会测量组的组长,6个交会点中最危险最艰难的西绒布交会点就由他负责。4月底的一天,他带着两位藏族向导到西绒布踏勘,中午时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能见度只有一两米远。回营的必经之路上还有一条10米宽的冰裂缝和坡度超过60度的悬崖,在这样的天气下,安全回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午五六点钟,狂风暴雪弥漫了整个珠峰地区,张建华依然没有归来,大本营和二本营所有队员都焦急万分。有人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有人用测量仪器中的几十倍目镜寻找……可他仿佛消失在茫茫雪海中,无声无息。 风雪迎面吹来,让人很难睁开眼睛,张建华和两名向导在中绒布冰塔林中迷路了,甚至他们也走散了。张建华不停地呼喊,偶尔能听到一两声回应,他就循着那声音往前走,可走啊走啊,还是看不见人,也看不清路。有那么几个瞬间,他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觉得自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片美丽却令人绝望的冰塔林了。7点多,雪终于停了,张建华走一会儿、爬一会儿,竟然奇迹般地从冰塔林里出来了。当他看到队友们在石头上做的测量点位标记时,知道自己有生还的希望了,坐在雪地上放声大哭。晚上9点多,筋疲力尽的张建华终于回到了二本营,他的裤子已经在碎石上磨开了许多口子。看到他,兄弟们都哭了。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并没有让张建华退缩,随后他又连续三次冒险穿越冰塔林,到西绒布交会点测量。登山队员登顶前后,他啃干粮、化雪水,在那里坚守七天七夜,完成了自己肩负的任务。 …… 4月17日 珠峰大本营 多云 今天是我住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夜晚,此刻,狂风正吹着帐篷哗哗作响。 今天的白云和蓝天都闪耀着荧光,云一层一层,山一层一层,有时,天的蓝色也一层一层。早晨离开白坝村时,远远看着卓玛日山就像一个金字塔,在群山中十分特别,难怪协格尔曲德寺修建在上面。 翻过加吾拉山口,喜马拉雅诸峰都蒙着云的面纱,只有珠穆朗玛的峰顶露在外面。从山口,我们一路下坡,到扎西宗乡后道路分岔,我们没有往珠峰大本营方向,而是继续下坡,前往曲当乡。海拔不断降低,从5200米到3660米,拉萨的高度。路边的草滩渐渐泛出青色,成群的牛羊在河边吃草。 快到曲当乡时,我看到一座雪山黑白条纹交错,就像是一匹斑马,又像是孟加拉白虎,卧在天地之间,十分神奇。在地图上看,那山的名字是亚静隆巴。 国测一大队一个水准测量组正在扎西宗乡到曲当乡之间测量。水准测量通常由水准已知点出发,沿选定的水准路线逐站测定各点的高差。2020珠峰高程测量的水准测量是从日喀则国家深层基岩水准点出发。去年12月,国测一大队的水准测量组就在西藏开始工作,经拉孜县一直推到定日县和聂木拉县,复测了珠峰地区的一等水准网。然后以此一等水准网为基准,从定日县和岗嘎镇分成两条支线,进行珠峰地区的二等水准测量,一直传递到珠峰大本营的水准基点。然后再以此为已知点,通过三等水准测量、高程导线、三角高程测量、跨河水准测量等方式传递到珠峰脚下6个交会点。待到觇标竖立在珠峰峰顶,各交会点通过三角测量,并和其他测量手段所得结果综合计算,确定珠峰的精准高程。 一等水准的精度高于二等,二等高于三等。但即使是三等水准测量,每公里的偶然误差也是毫米级。对误差要求极其严格,以保证水准数据的精确。我们采访的水准测量组,从扎西宗乡测到曲当乡,再原路测回去,如果数据误差达不到标准,就必须从头开始测量。 曲当乡水准测量组的组长叫吴元明,43岁,河南安阳人,副组长叫金良,32岁,陕西商洛人。 下午4点,扎西宗乡和曲当乡之间,六七级大风,人都有些站不稳,水准组开始准备测量了。他们找到公路边土地里三个大钉子般的尺桩,这是他们上午测到的位置。水准测量要避开正午,太阳直射不利于观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4点到8点,每半天被他们称为一个光段(多浪漫的名字啊)。在这里,他们每个光段能测3公里多。每段路线,都必须一步一步走。 金良把电子水准仪从仪器箱里取出来,让它适应环境温度,以最大限度避免热胀冷缩可能带来的影响。经过简单的调试,测量就开始了。风太大,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标尺固定在点位上。一个负责测距的工人,手持一个像是单轮手推车的测距仪,从点位出发,量12米,摆一个石子,再量12米,再摆一个石子。金良扛起仪器,用三脚架固定在第一个石子正上方。另外一名工人扛着标尺快步走到第二个石子处,先把一个金属的尺台放在地上,再把标尺固定在尺台上。这样,水准仪距离前后两个标尺的距离都是12米,用他们的术语说就是前后视距要相等。 金良把水准仪对准后方的标尺,观测、瞄准,读取并记录数据,转过头,再对准前方的标尺,同样的流程,就得出了这两点间的高程之差。他一挥手,扛起仪器就走,后方标尺的工人也扛起标尺就走,前方的标尺则保持不动。金良把仪器扛到不动的标尺前面第一个石子处固定住,而工人则把标尺扛到第二个石子处固定住。这时,刚才位于前方的标尺就成为后方的,而刚才后方的标尺则成为前方的,水准仪依然位于两个标尺正中间。就这样再重复刚才的测量流程,就这样,两个人轮流操作仪器,一段一段测下去。 路边是陡峭的山坡,堆满乱石,经常正测着测着,一块石头就滚落下来,有的是被风吹落,有的是被山上的岩羊踩落。有时,石头就滚过他们身边,幸好都有惊无险。 吴元明和金良住在曲当乡的马卡鲁峰宾馆二楼,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整个宾馆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房间里没有水,他们用水桶从楼下提水上来,饮用和洗脸都用桶里的水。吴元明说,这在他们外业工作中,算是比较好的住宿条件了。 去年12月,吴元明就到日喀则来测一等水准网,为珠峰测量做准备,一测就是40天。他说,那时天气更冷,更艰苦。测完回家过了个年,3月初,他又回来了。 国测一大队的车队副队长张兆义今年55岁了,性格开朗、直率,身上露着一股硬气。他这次负责我们记者团队的出行,担任我们的司机。张兆义参加过2005年珠峰测量,听说大队又要测珠峰,他第一时间给队长写了请愿信。他说,人一生如果能测两次珠峰,是多么自豪的事情。而吴元明也是第二次测珠峰了,他们两个曾在珠峰大本营共事。 两人见面,甚是亲热。吴元明说:“老哥哥,一晃15年了,都把你晃老了。” 张兆义说:“是啊,15年前我比你现在还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宁波测桥吧?” 吴元明说:“不是,是2002年骊山,兵马俑测图。” 张兆义说:“对,那一次真能把人热死。” 吴元明说:“还有2008年西部测图,我们在可可西里,比这苦多了。一提测珠峰,大家都觉得很苦,但咱们经历过的,有不少比这更苦的。” 离开曲当乡时,张兆义对我说,刚到国测一大队时,看到老前辈们受的那个苦,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哪是人受的苦啊。可当自己亲身经历了,完成了任务,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高兴。后来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字典里也就没有苦这个字了。 我们的车到绒布寺检查站时,张兆义下车办理通行手续,地上有冰,他脚下一滑摔倒了。我们急忙下车把他搀扶起来,问他要不要紧。他一瘸一拐地直说没事没事,继续驾驶前车带路。晚上在帐篷里,他撸起裤腿,我看到他膝盖和迎面骨上都流血了。 此刻已是夜里11点半,狂风依旧,我们的帐篷被风吹得左右摇摆。帐篷里住了6个兄弟,大家都已钻进了睡袋,但没有一个人入睡。晚上,大家都没敢喝水,怕起夜。 外面,除了营地几顶帐篷微弱的光亮,就是星星在云层中闪着的朦胧的光,珠穆朗玛隐匿在不远处的黑夜中。 我已经把睡袋摊开了。写完这几个字,出去方便一下,也钻进睡袋里去了。这第一个夜晚,不知是否能睡得安稳。但我激动而满足。海子写过:今夜,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让我彻夜难眠。 彻夜难眠又何妨。 4月22日 定日 晴转多云间有雪 天气很冷,虽然是晴天,中午出去吃面时,雪花在阳光里飘扬。 上午我在房间整理采访的素材,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杨帆,他一进屋就靠在墙上,哭着说:“看见测绘队员的手,我真受不了。” 原来他也在整理这几天拍摄的素材,看到前天在二本营拍摄的测绘队员们操作仪器的手部特写,看着那些黑乎乎、皴裂的手,他心疼地不能。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来定日后不久就听说一名叫谢敏的测量队员,父亲去世了,但他在山上手机没有信号,父亲遗体火化的那天中午他才接到母亲的电话,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一直在二本营和交会点上坚守着。前天我上去,他在点上还没下来。昨天下撤前,张兆义悄悄地对我说,来,我带你去见一下谢敏。我们走出帐篷,张兆义对着远处一群小伙子喊:谢敏。谢敏走了过来,张兆义先给他一个拥抱,拍了拍他的肩膀。谢敏是测二代,他的父亲和张兆义也是同事,因此,张兆义就像他的叔叔一样。谢敏转过头去,擦了眼泪。我看到他的整张脸都布满小小的裂纹,已经黑得不像样子,裤子上、鞋上全是泥和污迹。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我无法想象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在承受心理痛苦的同时,还能忍受如此的生理痛苦。我忍住了泪水,也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咱们这次一起下撤,好好休息,兄弟。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自从我工作以来,每年世界地球日的宣传都是一年中的大事。今年,由于珠峰测量宣传至今没有正式启动,这是我离地球日宣传最远的一年,但由于地球日的主题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又是我离大自然最近的一年。大自然啊,被我们称为荒蛮之地的所在,远离人类活动的所在,是多么真实,多么美丽。测绘队员长年和大自然相处,他们身上有无比可贵的真诚、单纯、简单和坚定,因此他们也配得上这大自然。 前天去二本营的路上,我看到三个易拉罐瓶子,捡起来装在背包里。返回时,周磊找到一个大垃圾袋,让我把易拉罐都装进垃圾袋,他提着,我们一路捡下去。到大本营时,垃圾袋装满了大半。 尼泊尔有个纪录片叫《珠峰清道夫》,画面触目惊心,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在洁白的冰雪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汇集珠峰,铝制罐头盒、饮料罐、鞋子、塑料包装袋,甚至暖水瓶、床垫。你可以想象天空堆满垃圾吗?你可以想象你的头顶堆满垃圾吗?正如纪录片里所说,如果珠峰死亡地带堆满垃圾,地球也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死亡地带。 不仅如此,整个亚洲机动车和工厂里排放出来的碳,正在喜马拉雅山脉沉积,碳可以吸收大气中的热量,降低阳光反射,一旦在冰雪当中沉积,冰川就会快速融化,对人类生存已造成重大威胁。 这次珠峰高程测量特别注重环保。大本营设有专门的垃圾回收站和环保厕所,实施垃圾分类,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清运,还有技术先进的厨余垃圾处理集装箱和污水处理集装箱。二本营也配备了环保厕所和垃圾分类收纳桶,工人定时将垃圾背运至大本营指定回收点。国测一大队还要求队员们,必须将在各交会点和测量线路上产生的垃圾和地面遗弃的垃圾带回。 今天午饭时,大家的话题都是定日如何如何舒适,简直像天堂一般。你一句我一句,有人说房间真安静,有人说可以随便上厕所、随便喝水了,有人说在床上能肆意翻身了,有人说不用整天都戴着帽子挡风了。而刚到定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里天气和住宿条件都比拉萨差许多。 写着写着又停电了,不知这次会停多久。没关系,毕竟这里,比大本营舒适多了。 5月27日 珠峰大本营 晴 直播仍在继续,接下来是峰顶测量获取数据的关键环节。队员们要在峰顶竖立起测量觇标,开展GNSS测量、雪深雷达探测和重力测量。指挥部的主角变成了国测一大队,大队长李国鹏显得紧张又激动,任秀波蹲在地上,不停地用对讲机与次落联系。 “次落队长,请报告GNSS接收到的卫星数。”任秀波说。 “大本营,卫星数56颗。”次落说。 突然,雪深雷达探测仪因线路接触不良出现问题,指示灯本应亮两个绿灯,却有一个绿灯变成了红色。 “大本营,雷达现在只亮了一个绿灯。”次落焦急的声音传来。 指挥部一下鸦雀无声,大家的心都跟着提起来了。 “请检查一下卫星接收机连接线。”任秀波转述一旁技术专家的话。 大家焦急地等待。过了一会儿,对讲机响了,次落在那头说:“好了,好了,两个绿灯都亮了,工作正常。”指挥部一片欢呼。 “重力测量完成。” “GNSS测量完成。” “雷达测量完成。” 随着次落一声声报喜的话语传来,指挥部所有人提着的心都放了下来。此时,队员们在峰顶已经工作了两个半小时,创造了中国人在峰顶停留的时长纪录。当次落报告完成任务准备下撤时,大家眼睛里都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的挥舞起拳头。我激动地使劲鼓起了掌,所有人都鼓起了掌。 我们的直播到中午1点半结束,持续了6个半小时。我从昨天傍晚到此时,一口东西都没吃,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回到帐篷,感觉精力和体力都已透支。可我计划好了要写一篇登顶测量的特写,直到下午5点,我才躺在床上睡了一个小时。 起来后恍恍惚惚。我很难形容那时的心情。刚刚经历的就像一场梦。开心?当然会有,但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强烈,甚至有些怅然若失。轻松?完全没有,还有报道任务没有完成。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只是尽自己的本职,去了想去的地方,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 人生就像一场攀登,幸运的人拥有更多攀登的机会,或者说幸运的人能在心里看见更多的山峰。我们会遇到坏天气,会遇到陡坡,会下撤,会失败,但攀登本身就是意义。面对星空,我常思考一个“庸俗”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有时我会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没有我们,阳光的意义是什么?山峰的意义是什么? 在出征前,我在报社的动员会上发言时就说,这次报道任务,对我来说无异于一次攀登。如今任务接近尾声,我无法评判自己攀登到什么高度。但我坚信,在攀登过程中的收获,足以让我受益一生。我重拾勇气,我摆脱了懒惰,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我结识了许多好兄弟,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星空和美景,这一切都令我更加相信人生中除了庸常,还有飞翔的,在高处的。我们生而有翼,为何要匍匐在地? 5月27日,注定要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天黑前,我接到任洪渊老师的电话,我最尊敬的老师。他的声音依然那么温和,他说:少勇,我的好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最近一个多月身体状况不太好,去医院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你不要忧伤,人生就是这样,我现在心情非常平静。我走在大本营的乱石上号啕大哭。我还盼着回到北京和他相聚,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对谈。现在我只希望任老师能少些痛苦,能挺过这一关。 任老师一生高贵,一生飞翔,一生攀登在高处。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座高峰。 我爱那些有坚持、有方向,真诚而高贵的人。 昨夜我还开玩笑说,既然明天是新年,今夜就是除夕。我有很多缺点,我也做过很多错事,这让我深深惭愧。除夕,我希望这次攀登,能除去我往昔的不堪,能让我勇敢而真诚地生活下去。 6月4日 拉萨 晴 我是在西藏登山学校见到扎西次仁的。登山队和保障团队都撤下来了,今天是清点物资的日子。攀岩训练场上摆满了各种帐篷和登山装备。扎西次仁正在一个角落里,弯腰检查着什么。 这几天网络上流传的、测量登山队员在珠峰峰顶竖立起觇标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他不仅是一位高山摄影家,也是人们眼里的登山天才,今年刚刚刷新了国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纪录——15次! 2003年,在人类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之际,21岁的扎西次仁也第一次问鼎世界之巅。作为日喀则市江孜县一个牧民家庭的孩子,扎西次仁从小在山上放牛、放羊,对大山有着深深的感情,珠穆朗玛更是他在心中时刻仰望的神圣之地。初中毕业后,扎西次仁被选拔进西藏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在体育运动学校读书的三年时间里,他表现优异,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在登山方面的天赋展露无遗,每次爬山都比其他同学快很多。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将他推荐到西藏登山学校,他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在西藏登山学校,扎西次仁依然是佼佼者,在校学习期间便参与了多次重要的登山活动,渐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攀登者。 我问扎西次仁,今年是不是他感觉最难的一次? “今年天气变化无常,又受到气旋风暴‘安攀’的影响,导致我们错过了前两个窗口期,确实困难很大。”扎西次仁说,攀登珠峰第一个难点是北坳冰壁。今年测量登山队第一次向峰顶发起突击时,修路队员沿北坳冰壁只攀登了一百多米,就发现积雪过深,有发生流雪雪崩的危险,为了确保安全,队员们全体下撤。 第二个难点是7028米北坳营地往上的大风口和7790米营地。测量登山队员在7790米营地扎营时,遇到了强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搭起了帐篷,虽然用绳子和岩石钉固定了,但在风中依然剧烈摇晃。3名队员挤在一个帐篷里,用自己的身体压住即将被掀起的帐布,几乎都一夜没睡。 而从8300米营地向峰顶进发时,原计划四五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用了9个小时。上面积雪依然很厚,刚刚修好的路——安全绳,被埋在了雪下面。队员们要不停地把绳子从雪里拉起来,相当耗费体力。风也很大,风夹裹着雪迎面而来,吹在脸上、眼睛上,生疼。因为是夜间,如果戴上雪镜更看不清道路,队员们顶着风雪,忍着疼痛,一步一步踩实了往上走,每一步都很艰难。 “今年攀登珠峰,对我来说意义特别重大。因为珠峰高程测量是重要的国家任务,我能参与其中感到十分光荣。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要用自己所有的努力和力量去完成好这项任务。”扎西次仁的这番话,应该说出了所有登队的心声。 2008年北京奥运会珠峰点火仪式上,扎西次仁创造了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一个首次。在此之前,中国的媒体从未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时传回新闻照片。扎西次仁用手机传回点燃火炬的照片迅速由新华社发布,被全世界各大媒体转发。从那以后,扎西次仁开始了自己的高山摄影生涯。他说,只有用心去拍摄,才能拍出好作品,不能光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要真心去喜欢它。他还说,高山摄影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因为你不能只在一个角度拍摄。队伍行进时,你一会儿要在最前面拍,一会儿又要在后面记录。有时,你还要爬到别人不必爬到的地方,只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角度。看得出来,他对摄影和登山同样热爱。 在登山学校,我还见到了测量登山队中的另外两位英雄,普布顿珠和次仁罗布。测量登山队在峰顶停留150分钟,创下了中国人停留时间最长纪录。而普布顿珠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方便操作测量仪器,都没有戴氧气面罩。6月1日下午在拉萨召开的媒体见面会,特邀了普布顿珠参加,当记者们听到他的壮举时,都发出了惊叹声,镜头全部对准了他。而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在说起他无氧操作仪器的故事时,几度哽咽。 次仁罗布是测量登山队中年龄最小的,今年是他第一次登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首次在珠峰峰顶测量重力值的重力仪,就是他一步一步背上去的。 说重力仪是这次测量中最难携带的仪器一点儿也不过分。它很沉,重达15公斤。由于测量原理的因素,它又很“娇贵”,在搬运过程中要尽量不倾斜,更不能倒。因此在攀登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身体姿势,每一次弯腰、每一次迈步,都比别人耗费更多的体力。次仁罗布说,它比婴儿还难照顾,孩子还有睡觉的时候,可它,得随时照看着。在7790米营地的帐篷里,为了防止重力仪在大风中倒地,次仁罗布硬是把它抱在怀中,抱了一夜。说起这些时,他腼腆地笑了笑,仿佛在说一件无比寻常的事情。 离开登山学校时,扎西次仁送我一本他的摄影作品集《喜马拉雅之子》。影集印刷精美,里面有登山队员的照片,还有自然风光的照片。最近几年,扎西次仁越来越注重记录珠峰与绒布冰川自然环境的变化。 “登了这么多次珠峰,得到她这么多恩赐,我无以为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希望更多的人保护珠峰的生态。”他、普布顿珠和次仁罗布,有一个共同点,眼睛如高原湖泊,说话时全身都散发着真诚。 他们都是喜马拉雅之子。 1、2020珠峰高程测量真实记录,一部诞生于极寒与风雪的英雄传奇。 2、作者有多年的野外测绘采访与跟队经验,文笔流畅,语浅情深。 3、全书配有精美的彩色插页,珠峰的草木白雪、朝阳日暮徐徐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七次大规模测绘与科考任务,中国测绘登山队员再战珠峰之巅。三次冲顶,险象环生。随队记者全程记录,让读者身临其境。致敬所有勇攀高峰的英雄,献给所有不屈与纯粹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