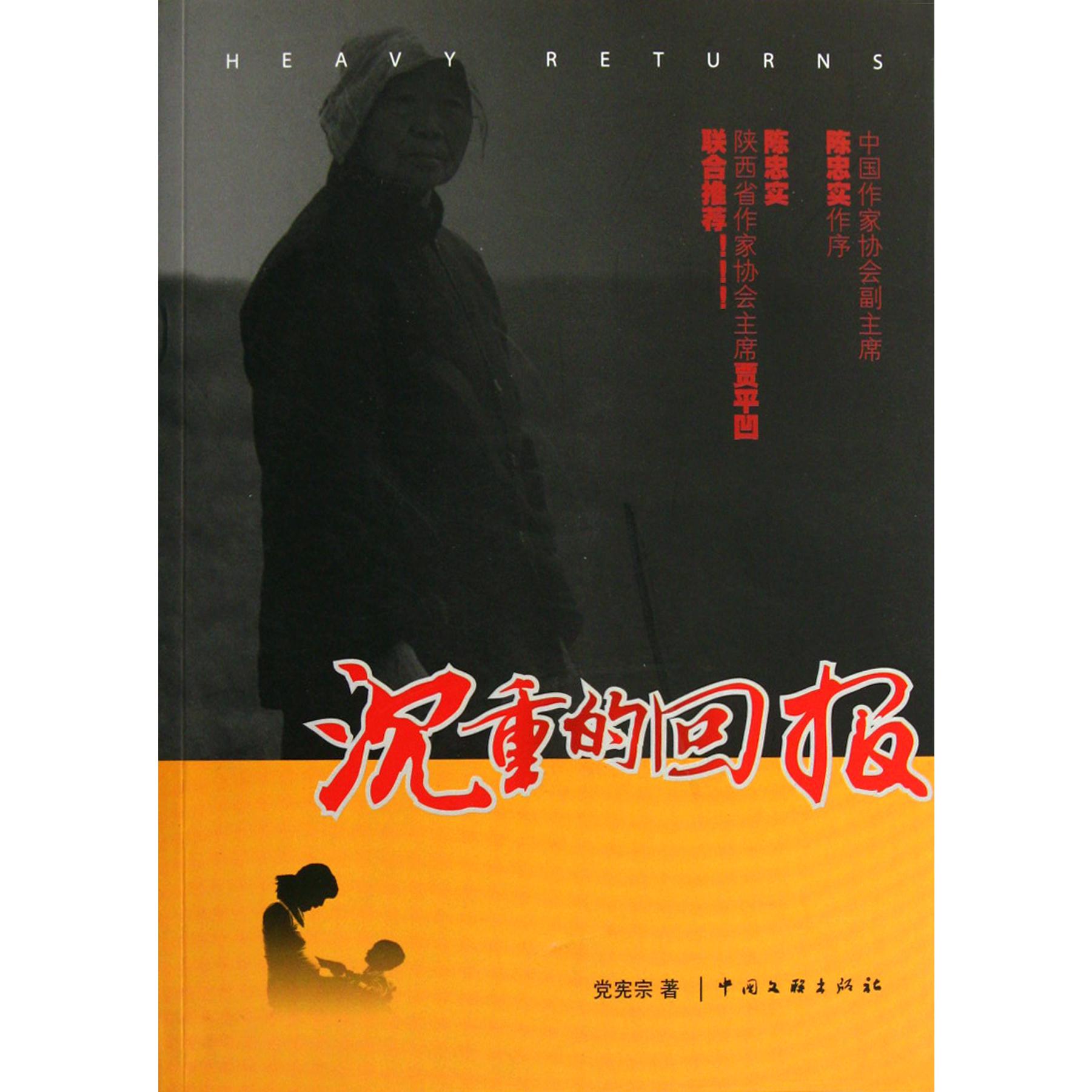
出版社: 文联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3.30
折扣购买: 沉重的回报
ISBN: 9787505967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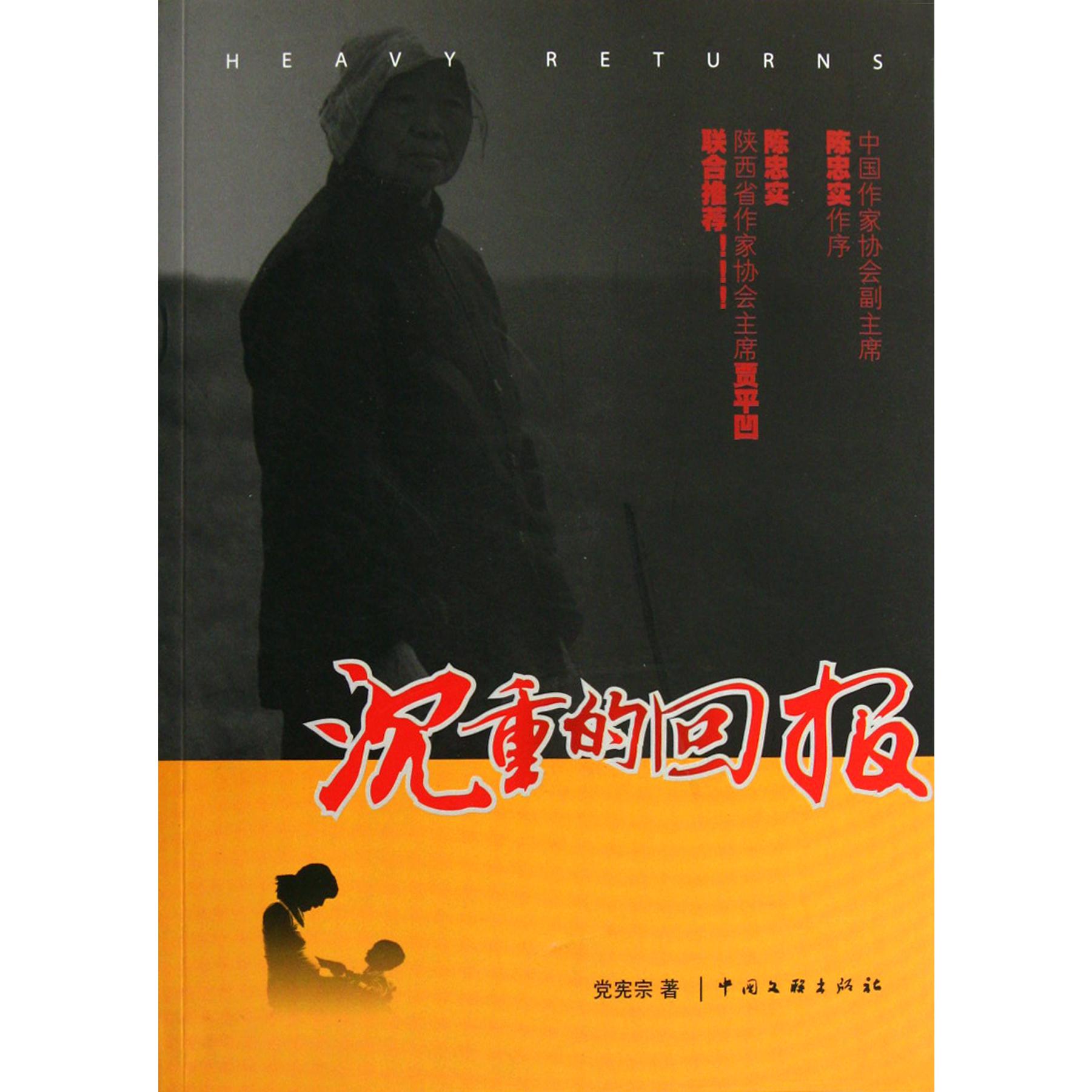
党宪宗,陕西省合阳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关雎诗社社长,《关雎诗刊》主编。党宪宗酷爱诗词创作,有时写散文。已在全国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诗词二百余篇,好多诗词已被选编入册,正式出版。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沉重的母爱》获得陕西省渭南市“五个一工程奖”,著名作家贾平凹曾书赠党宪宗为“人民诗人”。
儿子不是龙,是一条忤逆虫 母亲守寡含辛茹苦耗尽一辈子心血供养儿子成了龙,又供养了 孙女,供养了两个重孙子。儿子成龙后抛弃了农村的妻子,抛弃了女 儿,另觅新欢。城市的妻子五十多年只回过三四次家,城市的孙子也 很少回农村的家。他束手无策,情之无奈……他守在母亲灵堂前追 忆着往事。七十多年的恩恩怨怨、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王望龙呆呆地站立在老槐树下。天下着毛毛细雨,渭北的初春 还是一派萧条景象,树木还未发芽。零星雨点透过干枯的枝权洒落 在王望龙的头上,脸上,身上。王望龙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搅合在一起 往下淌,几根稀发贴在王望龙的头顶上,敞开着褪了色的土黄色风 衣,风衣被寒风掀起了衣角,显示出这个站在老槐树下被雨淋着的人 不是一般人。 王望龙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得从车上下来,取了一把伞给王望 龙。王望龙摇摇头没有接,用左手抚摸着裂开了膛的树身,看着看着 泪水又涌了出来。王望龙看了看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棵老槐树不 知伴随了多少代人,伴随着我已走过了七十年历程。” 我和王望龙虽然说在一个学校上过学,但相差四五级,在学校并 不认识,多年后在母校的校庆会上认识了,从此书信来往较多,两个 人的关系也就近乎了。王望龙在外省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很少回家, 这次因为母亲去世了,在家多呆了几天,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让我 今天早晨到村上接他,送他到咸阳机场,然后坐飞机回去。 王望龙的母亲活了89岁,今年农历二月初二去世。去世的第二 天傍晚,王望龙才赶回来。回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这个大孝子 无从下手,自己也感觉到无话可说。前妻的女儿王华见到了父亲,趴 在奶奶的灵前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奶奶,我爸回来了,我爸回 来了……”王望龙木然地跪在母亲灵堂前,望着灵桌上供奉着母亲 遗像。遗像还是母亲前年住院时拍的。按当地风俗,父亲去世已经 66年了,灵桌上一定要供奉着父亲的遗像。但那时穷乡僻壤哪有照 像的,何况父亲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猴儿王”。母亲的命真苦啊,一 辈子守寡,孤苦伶仃,死了还是孤单一人。王望龙想到这里,不由得 趴在地上大声号啕起来,号啕到伤心处,把头磕得砰砰响。王华看到 父亲难过的样子,哭的声音更大了。 晚上的小山村本来就很静,父女俩凄凄惨惨的哭声传到院里,传 到巷里,传到四邻。心软的姑姑婶婶们免不了又要掉泪,王婆婆真是 太恓惶了!父女俩正哭得不可开交之时,管事的村支书发话了:“不 要哭了,商量大事吧。”王华先止住哭声,拉起了父亲。支书说:“望 龙叔,昨天等你没有等着,我王华姐请来阴阳先生,埋葬日子定在二 月初八,搁七天,够长的了。我王奶奶一辈子受的苦在咱方圆十里再 没有。我王华姐的意思老人家在世就这一回了,现在就等你点头定 事呢。”王望龙心里的悲痛还没有转过来,又听支书说母亲受的苦方 圆十里再没有,心里更是悲上添悲了。母亲受了这么大的苦,都怪养 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支书说的“定事”,就是要自己往出掏钱。望 龙没说话,拿来旅行包,从包里边取出三万元交给女儿王华说:“这 是三万元,一切你和支书商量着办,家乡丧事风俗我不懂,钱不够有 我。” 三万元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王华接钱的动作显得缓慢而 沉重。她望了望奶奶的遗像,心里说:“这三万元算是儿子对母亲的 报答了!” 夜深了,梁山脚下的王家坡静静地躺在梁山怀抱里。天地黑得 像墨汁涂抹了似的,北风刮得院子里的干桐树枝“扎扎”作响。王望 龙穿着孝衣,头上缠着孝布,紧挨着母亲的头,坐在母亲生前最爱坐 的柳条椅上。按当地风俗,儿女守丧必须跪在地上,谁能跪上几天几 夜呢?时间长了,儿女们都坐在铺着谷草的地上。王望龙70岁的人 了,坐也坐不下来。王华特意给父亲搬来奶奶生前坐的椅子,让父亲 坐着守丧。王华想:“父亲能给奶奶守丧,这已经是奶奶的福分了。” 王望龙靠着椅子背,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望着母亲的遗像自言自 语地说:“妈,你望子成龙,望子成龙,你儿子成了龙对你有什么好处 呢?你这个不孝儿子自走出家门上了大学,几乎没有陪过你一个晚 上。你死了,儿子却陪着你。你说话呀,妈妈!你有什么委屈对儿子 说呀……”王望龙说着说着泪水又塞满了眼睛。 王望龙的老爷爷是个举人,爷爷是个秀才。父亲虽然没有赶上 清朝科举,却也读了不少书,识了不少字,只是光景一代不如一代,到 了父亲的手里,家里已穷得叮当响。父亲靠着识了几个字,当了教书 先生。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子孩子少,收入更少,日子过得吃了上顿没 下顿。幸亏王望龙的母亲精打细算,加之家里人少,攒前挪后,日子 也将就地过着。王望龙的外爷也是个穷秀才,家住李家坡,和望龙爷 爷是同窗。两家文相对,穷相近,王望龙父母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两小 无猜,却也是隔三岔五相见,两个人早已互相喜欢,结婚后更是恩恩 爱爱,甜甜蜜蜜。 灵堂前的蜡烛扑闪扑闪地闪着。王望龙看着将要熄灭的蜡烛, 烛泪流了一大堆,残余的烛身半边已经塌陷,烛芯完全裸躺在蜡液里 挣扎地燃烧着,最后灭了。蜡烛熄灭的整个过程是那么不甘心,蜡烛 多么想死芯复燃,但还是灭了!就这根蜡烛来说,永远是灭了!人常 说“人死如灯灭”,母亲的生命也就和这蜡烛一样,永远灭了!王望 龙坐在漆黑的灵堂前,黑暗给王望龙带来一点轻松,什么也看不见, 王望龙实在无颜面对母亲呀!谁知王华又拿来了一根点燃着的蜡 烛,插到烛台上说:“灵堂前的蜡烛不能灭。爸,你睡吧,让我守着。” 王望龙摇了摇头,王华也没强求,心里说:“你守上三年也还不清我 奶奶的债!”王华顺便坐在灵堂前奶奶的脚下。王望龙看着坐在灵 堂前的女儿,又看了看母亲的遗像,心里一酸,泪又流了满脸。 王望龙的小名叫龙龙,四岁时能背诵唐诗四五十首。龙龙的母 亲识字也不少,还能写简单的信。父母俩对这个宝贝儿子疼得要死, 爱得要命。龙龙三四岁,父亲给学生上课时就领着儿子到课堂上听 课。龙龙也听话,和那些大孩子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三字经”、 “千字文”居然比那些大孩子记得还快,记得还熟。父亲相信儿子长 大一定有出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龙龙六岁时, 父亲上山砍柴摔死了。父亲咽气时,一手拉着龙龙,一手拉着妻子, 断断续续地说:“再苦再难都要供龙龙读书,龙龙一定能成龙,儿子 的名字从现在起就叫做望龙吧!” 父亲死后,母亲难过得从死里走了一回,人瘦了几十斤。母亲那 时才25岁,年轻轻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咋过呀?第二 年,本族的大伯劝母亲带着望龙改嫁,母亲一口回绝:“我生是王家 人,死是王家鬼,我一定要把龙龙抓养成人!”从此,王家坡这个小山 村,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一个年轻女人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进学堂, 晚上又接孩子出学堂。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