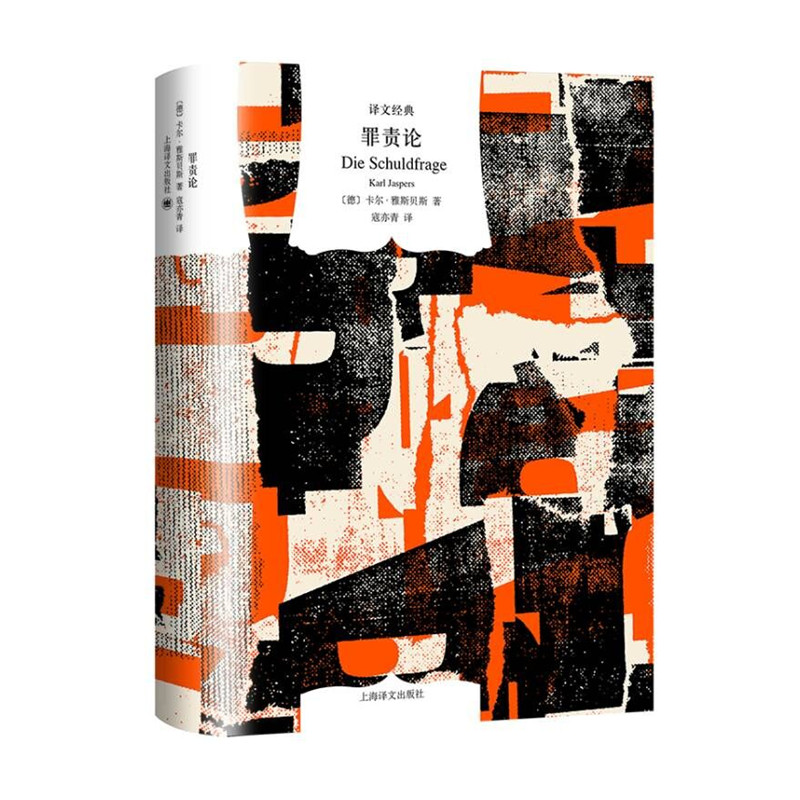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1.20
折扣购买: 罪责论(译文经典)
ISBN: 9787532792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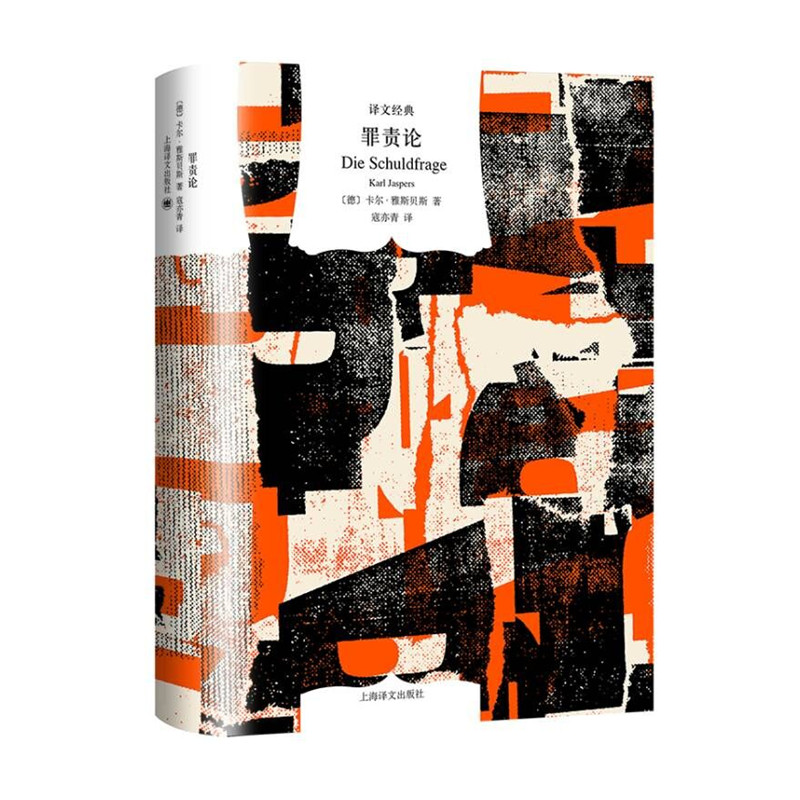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16年任海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1921年被聘为该校哲学教授。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职。1948年至1961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3卷,1932)、《生存哲学》(1938)、《论真理》(1947)、《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哲学导论》(1950)等。 "
"【精彩书摘】: 作为一个德国人,通过书中的论述,我想辨明事实、寻求共识;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努力探寻真相。——前言 慷慨激昂的审判并不难;难的是平静的回顾。固执己见、中断交流并不难;难的是超脱个人立场、坚持不懈的探索真相。抓住和坚持一个想法,对其他思想嗤之以鼻并不难;难的是循序渐进的进步,永不抗拒新的质疑。——导论 在彻底的坦率和真诚中才能找到我们的尊严——即使在无权的状态,其中也蕴藏着我们唯一的机会。每个德国人都应该问自己,他是否愿意走这条可能通向彻底失望、继续受损、被当权者轻易盘剥等种种危险的道路。答案是,这是唯一一条能让我们不至于沦落为灵魂贱民的道路!——导论 当负罪者感知到道德的失误和灵魂的创痛时,他受到了内心的指责,由于道德和灵魂的罪责是引发政治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根源,所以也与政治罪责和刑事罪责相关。——A 罪责分类提纲 道德罪责只能由当事人自己——而非他人——来判定,他人只能通过善意的争论让其认识到罪责。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他人进行道德审判,除非他出于关切将自己代入对方的角色。只有视人如己,才能拉近距离,在自由的交流中取得共识,最终每个人独立完成对自己的道德评判。——A 罪责分类提纲 纽伦堡审判不是唯一的重要事件,就本质而言,它是政治重建中有意义的一个环节,也许整个过程会受到谬误、愚蠢、冷酷和仇恨的干扰——也许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最终将屈从于目前制订规则的强权。设立纽伦堡法庭的同盟国对外表态,它们将共同建立一个遵守国际秩序的世界政府。它们发誓将履行对人类的责任,作为二战的果实,而不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这样的誓言不像是虚假的誓言。——B 德国问题 民族责任感的内涵远比盲目顺从统治者更为深远。如果祖国的灵魂被毁灭了,它就不再是祖国。国家权力并不是效忠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摧毁了德国的本质,它反而是有害的。——B 德国问题 看上去最不可能犯罪的人却犯下罪行,他们可能是家中的父亲,勤勉的公民,平时兢兢业业地干各种工作,现在也兢兢业业地在集中营里杀人,或者遵照命令干出其他暴行。——B 德国问题 政治自由的起点是,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对国家政治负有责任,他不光有个人好恶,还有主动参政的意识,他不会随意听信别人以恶意或者愚蠢虚构出来的建设“人间天堂”的政治信仰,他清楚地知道,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政治家应该走一条有可行性的道路,以人性以及自由的理念为指导。 一言以蔽之,没有灵魂的自省,就没有政治的自由。——B 德国问题 " "【编辑推荐】: 死亡恐惧下的人性底线 极权废墟上的良知反省 重塑德国战后国民道德的经典之作 "
死亡恐惧下的人性底线 极权废墟上的良知反省 重塑德国战后国民道德的经典之作
书籍目录
《罪责论》中文版序 徐贲
罪责论
前言
以德国人精神状态为主题的大学系列讲座导论
罪责论
A 罪责分类提纲
1 四个罪责概念
2 罪责的后果
3 权力,权利和宽宥
4 审判者,被审判者和审判对象
5 申辩
B 德国问题
I 对德国人罪责的区分
1法律罪责
2政治罪责
3 道德罪责
4 灵魂罪责
5 综述:a) 罪责的后果
b) 集体的罪责
II 辩解的可能性
1 恐怖主义
2 罪责和历史背景
3 他人的罪责
4 所有人的罪责?
Ⅲ 自我反省
1 对反省的逃避
2 反省之路
1962版《罪责论》后记
德国联邦议院关于纳粹德国大屠杀罪行追诉时效的辩论
(1965年3月10日与25日)
参考文献
试读内容
【在线试读】
1962年版《罪责论》后记
这原是一篇写于1945年的讲课稿,我在1946年1月和2月的大学课堂上宣读了讲稿,后来它又被正式出版。这篇文章让我们回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德国人每天面对着暴风骤雨般的指责。除非谈公事,美国士兵被禁止和德国人交谈。德国民众现在才完全了解纳粹德国的罪行,当时我对纳粹罪行的计划性和规模性也认识不足。那时大家都活得非常辛苦,不管留守在家里的人,还是后来被送往各地的战俘们,或者被驱逐的人。老百姓束手无策,沉默无语,心中压抑着愤懑,在某个时间段里也许还显得麻木。许多人想从战胜国那里为自己捞点好处。有人抱怨悲叹,有人铤而走险。人们只能从家人和朋友身上得到些许温情。
我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个人的思考成果:在承担业已明确的罪责的同时,德国人应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尊严?文章还提到了战胜国应该承担的罪责,提及这一点,不是为了帮德国人脱罪,而是为了维护真理,捍卫个人的合法权利,使德国人免受政治上的迫害。这篇文章能在盟军占领区公开出版,本身已经证明,同盟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具备自由的精神。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曾经对我说,我的文章不仅适合德国人看,也适合让同盟国的国民看。我曾经努力帮助德国人找回自我,让他们能重新呼吸清新的空气。这篇文章也有助于德国人和战胜国的人民重新建立起友谊的纽带。
虽然那时资料匮乏,但愿意了解真相的人都很清楚纳粹政权的基本特征:狡猾的策略,彻头彻尾的谎言,罪恶的企图。重获新生的德国人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书中的论述大体是正确的,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在看待当时刚建立的纽伦堡法庭的问题上,我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念是伟大的。那时我们已隐约看见,改变人类世界的某种东西似乎在未来闪烁着微光——世界各大强国团结起来,对罪名确凿的战争罪行施以严惩,从而确立了国际公理,创造了新的世界格局。从此之后,任何政治家、军队将领和官员都不得以国家利益或者命令为借口。所有的国家行为都必须通过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个人——可能是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来完成。国家元首的职权归于国家,其本身仅是一个神圣而非凡的象征。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国家犯罪由某些特定的人承担罪责。命令和服从包涵着必要性和荣誉感,但服从命令的人不能在明知它是犯罪的情况下执行命令。国家层面的政治誓言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那就是它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或者针对某个有自身的目标和理念并已向公众宣布的团体,不能把政治和军事机构的某些人作为效忠对象。个人的责任永远不会终结。虽然世界上存在激烈的冲突,但犯罪事实是很容易辨明的。当我看到犯罪的可能性和犯罪开始的迹象,犯罪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当人们在某个地方听到这样的呼喊声:“德国觉醒,犹大去死!”“现在要有人头落地!”当希特勒向波滕帕谋杀案 的凶手发出贺电时,即使犯罪尚未成为事实,公众尚未参与进来,人们的良心就应该发出警告了。按照新的理念,凡下命令或者执行命令造成犯罪的人,都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审判。以这样的威慑手段维护和平,人类以通俗易懂的道德为纽带团结起来。这样人类才不会再重复我们的遭遇:在自己的国家里被剥夺尊严,失去人权,被驱逐和谋杀,却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自由国家竞相讨好希特勒却背叛了德国人民,自由国家的公民成群结队地来到柏林参加奥运会,各国在经济会议和文化活动中接待纳粹德国认可的人,而拒绝接待受纳粹德国排斥的人——这样的历史才不会再重复。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不会再次出现:当1933年尤其1934年德国发生大量暴行后,其他自由的欧洲国家没有团结起来,使用和平的武器进行对抗,反而以“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借口百般容忍。当一个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欧洲邻国相差无几的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灾难——即使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欧洲诸国不应坐视不理,任其国民落入恐怖主义的暴君手中,它们应该伸出援手,就像邻国遇到自然灾害时一样。
新的时代开始了。法庭已经成立了,我们期待它的发展。人类永恒的愿望将要得到实现。也许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虽然我年龄不小了,对政治有相当的了解,但我仍寄予期待。我已经明白了那时我尚不清楚的东西,在此我更正从前的判断。
苏联也参与了法庭审判,就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而言,它与纳粹国家并无区别。也就是说,有一个审判者事实上并不承认纽伦堡审判的立法精神。法庭的调查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已知罪行,而是针对被告人的具体行为。法庭上的起诉不包括“不知犯罪主体的罪行”,这个规定并不会引起麻烦。法庭的审判对象局限于战俘。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没有军事目的的破坏行为也没有受到法庭的调查。
1945年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但没有表达出来。虽然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遭受了相当过分的破坏,我仍对自己说,战争双方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全心全意为纳粹国家卖命的民众不要指望得到仁慈的对待。当年,来自被压迫民族的数以百万的奴工被运送到德国;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毒气室的火车每天都在运行;西线战役打响后,鹿特丹的市中心遭到损毁;考文垂遭受毁灭式轰炸,按照元首的话,“我要彻底摧毁他们的城市”;全世界受到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恐怖政权的威胁。面对上述种种肆无忌惮的暴行,盟军的基层机构很难保持分寸。执行机构——也许在未经本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实施了没有军事必要性的行动,对德国民众进行恐怖打击,以报复德国政府的暴行,这并非来自自由国家高层的授意。如果此类罪行也能得到审判,它将作为伟大的事件载入史册,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也将随之改变。从前我就应该表明我的这一看法。
在英美的法治思想指导下,起初纽伦堡审判的程序是令人信服的。对被告人的第一场庭审是无懈可击的(我不想谈论剩余的几场庭审)。法庭想要找出真相、伸张正义,犯罪行为有明确的司法定义。法庭只对犯罪行为——而非遭人唾弃的道德行为——做出审判。因此沙赫特(Schacht)、巴本(Papen)和弗里奇(Fritsche)被无罪释放,虽然法庭也宣读了对其行为的道德审判的判词。有意思的是,来自苏联的法官提出了异议,他反对无罪释放的判决。他低劣的法律意识使他无法区分司法和道德的区别。这位法官只是作为胜利者进行审判,而其他国家试图限制战胜国的权力并付诸于行动。
但是希望落空了。像从前一样,伟大的理念仅止于理念,而没有成为现实。纽伦堡审判并未通过国际法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
由于纽伦堡审判没有遵守它的承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曾经写道:“……那么纽伦堡审判将不是一次赐福,而是引发灾难的一个要素。这场审判是不是一场装模作样的虚假审判,世人自会做出判断。后一种可能性不应该成真。”现在我不能收回当时的判断,虽然纽伦堡不是装模作样的表演,它在法律形式上无懈可击,但它仍是一场虚假的审判。它事实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它不是建立在各战胜国共同的法权状态和法律意志基础之上。因此它走向了自身意愿的反面。法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增长了人们对法制的怀疑。对于伟大事业的怀疑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坚持伟大的理想,但不能脱离过去的经验。当今世界,缺乏法治精神的政权正在日益强大。世界还远未像纽伦堡法庭设立之初所期望的那样获得安宁。世界的安宁有一个前提,它依靠法律的保障,需要甘愿屈居法律之下的世界大国倾力维护。它不会从寻求安全和消除恐惧的动机中自动产生。只有通过不懈的勇敢行动,保持对自由的向往,人们才能不断重建世界的安定。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有身份和尊严的精神道德生活为前提。这是它的基础,也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