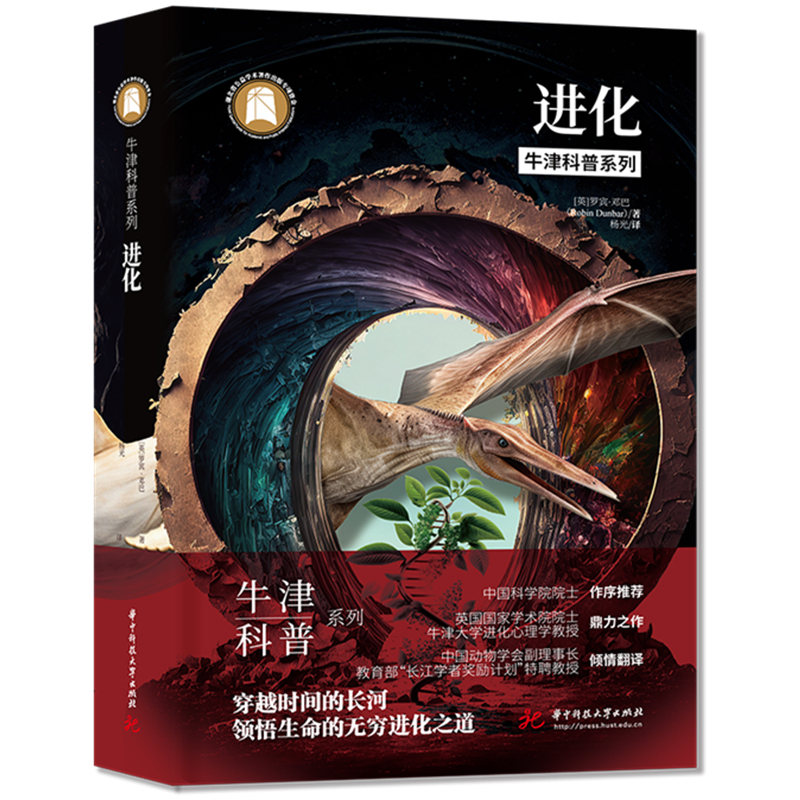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4.80
折扣购买: 进化
ISBN: 9787568098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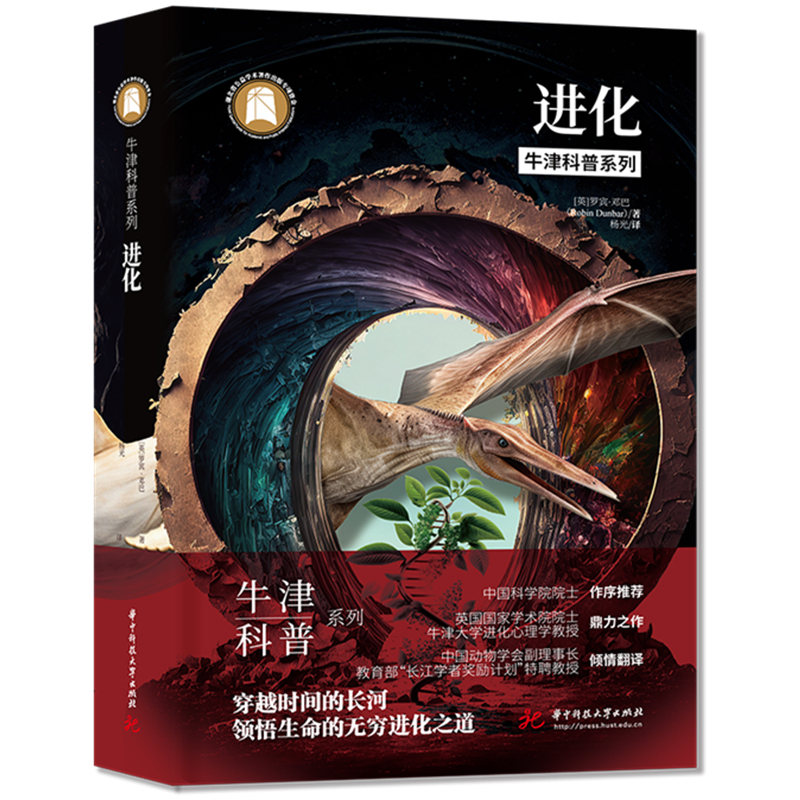
作者 [英]罗宾·邓巴(Robin Dunbar)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百年研究项目联合主任,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心理学会会员。提出了社会脑假说、邓巴数等著名理论。 译者 杨光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个重点项目,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暨生物进化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生态学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长等,担任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Integr Zool,The Innovation,Scientific Reports等国际著名期刊编委。
基因真的是自私的吗? “自私的基因”一词因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同名书而广为人知。这只是对自然选择过程的一个隐喻:在自然选择作用下,基因的表现显得它们好像是自私的,但并不是基因自身自私。基因对自身所做的事情并不比其他任何化学物质更有意识。基因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除了作为代表性状的代码)。自然选择是一个盲目的过程,导致一些基因在后代中有不同的表现,而另一些则没有。但是,由于我们极度习惯根据个体的意识来思考人类世界,如果我们认为一些基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在后代基因库中的比例,那么我们在心理上就更容易理解像进化这样以目标为导向的过程。基因的表现看起来是有目的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基因的表现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这可能并不总是正确的,例子有很多。一个例子是多细胞生物(换句话说,大多数比病毒和细菌更先进的生命形式)可以从其基因的有效传递中受益。多细胞生物实际上是由许多不同的基因组成的复合物,这些基因协同作用以产生一个能有效繁殖的个体。任何基因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基因的利益,那么它不仅会自掘坟墓,也将使所有与其相关的基因走向灭绝。实际上,它必须与其他基因合作并“注意”它们的需求。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病原体。如果它们的毒性强到能杀死它们的宿主,那么不仅宿主的所有基因会灭亡,病原体本身也会灭亡。通常情况下,毒性较小的变种(或者说突变体)才繁殖得最好,因为它们不会杀死宿主并能产生更多后代。换句话说,这种病原体的基因库会越来越接近毒性较小的病原体,而不是毒性较大的病原体。当病原体与其宿主达成某种“共识”或达到稳定的平衡状态时,病原体的毒性减小是普遍现象。我们DNA中插入的许多病毒基因可能就是通过这一过程产生的。我们感染的许多致病病毒,其毒性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 在许多社会性物种中存在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个体的生存和繁殖及个体基因的成功传递依赖于与群落中其他个体的协作。这种协作可能是一起狩猎,或联合抵御捕食者(见问题81)。实际上,这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我们都因同意遵守契约而生存得更好。不履行职责的个体会破坏“社会契约”,从而导致每个个体都生存得不如它们本应该的那样好,最终会走向灭绝。这类个体导致“社会契约”变得不稳定,但如果能让“社会契约”发挥好作用,每个个体通常都会生存得更好(见问题73)。 尽管有这样的例子,但当我们思考自然选择如何起作用的时候,假设基因会以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发挥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才符合实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假设能非常清楚地预测一个基因或至少个体会如何表现。然后我们可以问,我们所看到的是否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就像科学一样,理论无法预测我们的所见时才是最有用的,因为理论确定了我们未知的内容。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并自问因我们的无知而可能遗漏了什么。这是科学方法的核心。 为什么我们不能长生不老? 从细菌到人类,所有的生物都会衰老和死亡。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自然选择难道不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永生吗?毕竟,寿命较长的个体比寿命较短的个体能产生更多的后代。有些树能活几千年,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呢? 事实上,我们人类如此渴望永生,以至于我们愿意把大量的金钱花在医疗、饮食和运动上,这些都是为了达到长生不老这个目的——有时候,我们甚至把身体深度冷冻,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医学会找到让我们起死回生的方法。尽管自然选择能带来有利的结果,但有三个相当明显的原因可能会让我们的希望落空。 第一个原因是,在繁殖投资和生存投资之间存在一种权衡:生物会选择以牺牲自身生存为代价,将一切豪掷于繁殖之机。太平洋鲑鱼、雄性袋鼬、海生猪鬃蠕虫和西非酒椰等物种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们把一切都投入繁殖中,然后精疲力竭地死去。问题是繁殖的能耗很高,而没有一种生物拥有无限的能量。繁殖迟早会将生物的能量消耗殆尽。性激素睾酮给男性生理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由此产生的损耗会显著降低男性的预期寿命。一项对过去500年来朝鲜皇室太监寿命的分析显示,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具有相似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未被阉割的男子长15~20年。同样,生育和养育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损耗,至少一项针对欧洲历史人口的统计学研究发现,女性的寿命与她生育的孩子的数量成反比。 第二个原因是身体会精疲力竭。正如前文所述(见问题38),人体器官会不断更新,但某些器官相对来说不易更新,当这些器官损坏时,就无法恢复了。更重要的是,突变可能随着每个细胞的复制而积累。此外,在生命后期表达的有害基因相较于那些在生命早期表达的基因将更少地受到选择的影响:后者的携带者还未繁殖即被杀死,而前者的携带者在自然选择之前就已完成了繁殖。器官损坏、突变积累、有害基因传递,所有这些过程最终将会消磨掉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却无能无力。 第三个原因是简单的偶然进化事件。有些生物的物质构造特别坚韧,这使它们能够活得更久,因为它们受损害的可能性较小。树木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生命形式之一。 据估计,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红杉有2000年的历史。塔斯马尼亚岛上休恩松的一些茎(见问题37)也有2000年的历史,整个克隆体可能有11000年的历史,但与邻近的金氏山龙眼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金氏山龙眼唯一幸存的克隆体大约有43000年的历史。 树木长寿的原因之一是构成树干纤维的木质素(尤其是最近发现的纤维素纳米晶,其强度是钢的8倍)特别坚韧,能够抵抗意外断裂和食草动物的攻击。然而,大多数生物并没有这种优势,因为由这些物质构造的身体有两个重要的缺陷。首先,这些物质使树木非常沉重,从而增加了运动成本(这就是树木不能移动的一个原因,尽管在《指环王》中树木可以移动)。其次,树干相对不灵活,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面对最强的风,它们也不会弯曲太多。如果你想在树上爬来爬去或逃避捕食者时身体能够扭动和转动,那么你不会愿意成为一棵树。 这都是不同选择间的权衡,其中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是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合理替代方案。这些生物学决策的复杂性使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远胜其他方案的完美解决方案。简而言之,通常有许多不同的方案可以最大化适合度。自然选择所能获得的最好结果就是劣中选优。 恐龙真的灭绝了吗? 在过去3亿年的大部分时间(爬行动物时代)里,恐龙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生命形式。然后,在大约6600万年前,它们突然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哺乳动物。“突然”是相对而言的,恐龙当然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而是在数万年的时间里逐渐消失的。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一个世纪以来地质学的标志性谜题之一。 1980年前后,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和沃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父子组成的地质小组注意到,恰好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都有一个薄而暗的地层。这一地层(在大多数地方只有几厘米厚)中有异常高含量的铱元素,这种化学元素在地球上非常稀有,但在小行星中含量丰富。该地层也充满了受到冲击的石英和彗星撞击地球而形成的结晶态熔融岩石的微小球体。他们认为恐龙的灭绝是由一次巨大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造成的。这个时期也涉及频繁的火山活动,特别是印度的德干地盾(一个2000米厚的熔岩区域,当时喷出的熔岩的总体积为100万立方千米),火山活动产生的冲击波在地球上回荡,并导致了地球另一侧的火山喷发。火山喷发释放的有毒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硫)和火山灰显著地强化了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气体和炽热碎片所造成的温室效应。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证实了上述观点。该陨石坑位于加勒比海西南部,直径150千米,深20千米,其南缘是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据估计,导致该陨石坑形成的小行星的直径为10~15千米。从墨西哥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海啸海床,以及更厚、更深的火山灰层(厚达1米,表明离撞击地点很近),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此巨大的物体在穿过大气层时产生的摩擦会点燃大气层,而撞击本身会将大量碎片抛向大气层上部。化石证据表明,距离该陨石坑5000千米之外的动物瞬间死亡并被掩埋。由此产生的尘埃云遮蔽了整个地球上空的光线,使地球陷入黑暗,并使大部分地面覆盖在火山灰中长达至少10年。在这种状况下,植物是不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据推测,北美洲有57%的植物灭绝了。附带说一下,有证据表明,在西半球同一纬度,可能有一排较小的撞击坑,表明一个更大的天体可能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解体了。如果事实是这样,其影响只会比推测的更大。 所有以植物为食的物种都会面临食物短缺的困扰,随即是以食草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据估计,第五次大灭绝事件中有超过75%的物种灭绝。以前“称霸”地球的那些物种全部都不见了,包括恐龙、蛇颈龙(海洋动物)、巨型海鬣蜥和菊石(与章鱼有亲缘关系的一类巨型软体动物,其壳的卷曲直径可达2米,经过切片和抛光后可作为装饰艺术品,因而备受珍视)。鲨鱼、魟鱼和鳐鱼的41个科中,有7个科在这个时期消失了。存活下来的物种主要是体型较小的杂食类、食虫类和食腐类动物。幸存下来的爬行动物是那些体重不超过25千克的类群(例如海龟、小鳄鱼和蛇)。 然而,的确有一群小型恐龙存活了下来,即现生鸟类的祖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恐龙从未灭绝过。它们中的一些仍然很快乐地和我们共存。当气候再次稳定下来时,鸟类和幸存下来的小型哺乳动物经历了迅速的物种辐射,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多数主要类群。即便如此,直到撞击发生后18.5万年左右,化石记录中才开始大量出现哺乳动物。 为什么尼安德特人的眼睛那么大? 尼安德特人最突出的特征是后脑勺上的“圆发髻”隆凸。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有这种不寻常的特征。事实上,这个“圆发髻”与尼安德特人的另一个特征有关——他们异常大的眼窝。尽管他们的大眼睛在过去偶尔会引起人们的讨论,但同样,人们从未做出过任何解释。这两个特征似乎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尼安德特人就是这样的。 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大眼睛和“圆发髻”被证明是相互关联的。这种解释与尼安德特人的另一个特征直接相关——他们生活在北回归线(目前位于北纬23°26′)以北的高纬度地区。在热带以外地区生活面临的问题是,白天通常很阴暗(因为阳光以特定的角度射入,必须穿过更多的大气层,而且正如北方人非常清楚的那样,北方的天空通常有更多的云层覆盖)。此外,随着与赤道的距离加大,白昼的长度越来越具有季节性,冬夜漫长而黑暗。这些因素让视觉变得更加重要,生活在这些纬度地区的物种往往拥有高于动物平均水平的视觉。 在这些情况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善视力,那就是增加视网膜(眼睛后部的感光层)的面积(见问题12),以便接收更多的光线。然而,这意味着整个眼球会变得更大,也意味着处理接收到的光信号的神经系统(包括连接眼球后部到大脑的神经元,以及大脑中分析和处理这些信号的区域)也必须成比例地增大,因为如果拥有一个有效的光接收机制而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去处理额外的信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尼安德特人不仅需要更大的眼睛,也需要更大的脑容量。由于处理这些信号的主要视觉区域位于大脑后部,所以你看到的是尼安德特人后脑勺的“圆发髻”。 事实上,我们甚至也可以在现代人中见到这种现象: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与热带地区的人相比,眼球更大(尽管远不及尼安德特人的眼球大),因此脑容量也更大。(我们没有尼安德特人那样的“圆发髻”脑勺,因为现代人还没有进化出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庞大的视觉系统。)虽然现代人脑容量的这种纬度差异已经为人所知很长时间了,但它的意义仍总是被误解。这与热带和高纬度地区人群的智力无关,因为智力与额叶有关,而不同纬度的人群之间的额叶大小并无差异。脑容量的纬度差异只是和视觉敏锐度有关。事实上,在现代人中,眼球(以及脑容量)的大小与人们生活的环境的光照水平密切相关。它唯一的意义是,热带地区的人到高纬度地区时在阴天无法像高纬度地区的人看得那么清晰,而高纬度地区的人到热带时眼球会被灼伤(这就是他们在热带地区更可能选择戴太阳镜的原因)。 现代人只在欧洲生活了大约4万年——只有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时间的1/10。非常了不起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捕捉到如此清晰的适应信号。这反映了当环境要求足够高时,选择能够加快进化的速度(见问题16)。这也提醒我们,环境对进化的许多影响是由气候驱动的(见问题17)。 尽管偶尔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大,但实际上他们脑容量的平均大小与现代人的大致相同,甚至可能更小一点。一个后果是,他们将如此大的脑容量用于视觉处理,其前脑的神经物质就会减少,而现代人大多数敏捷的思维活动是在前脑完成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前额比现代人的更倾斜,而现代人的高圆额头构造可以容纳更大的前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安德特人拥有和现代人一样大的脑容量,但尼安德特人制作的石器却远没有达到和取代他们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一样的水平(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尼安德特人从各种意义上讲已经是现代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尼安德特人很愚蠢。事实远非如此。如果尼安德特人不够聪明,不能找到应对冰期的严酷环境的方法,他们不可能在欧洲生存近40万年。 然而,这确实意味着,尽管尼安德特人比他们的祖先聪明得多,但并不如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聪明。现代人大约15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并于4万年前抵达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这些来自非洲的人类皮肤更黝黑(而且很可能是卷发,见问题68),使用着像针和纽扣这样精密的小工具,像弓和箭这样新型的武器,还有像标枪一样的长矛,并配备能极大提高投掷距离与精度的投矛器。尼安德特人大脑中较小的额叶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交能力较差,无法像现代人一样维持那么大的群体(见问题64)。这会对尼安德特人的生存能力产生各种各样的直接影响。 ①权威性。本书作者罗宾·邓巴是著名进化人类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百年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是“邓巴数”提出者;译者为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光,内容准确、权威。 ②前沿性。进化是生命进程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本书从进化的遗传机制、进化的生物学理论开始,然后从大到小介绍了生物、人类的进化历史,从实到虚介绍了人类生理、行为、心理的进化,内容前沿,探讨深入。 ③普及性。本书概述了与进化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包括进化与自然选择、进化与适应、进化与遗传等,并以大量详实的事例辅助验证理论,数据充分,语言通俗易懂,没有专业背景也能轻松阅读。 ④可读性。本书体例新颖,版式宽松,内配精美彩图,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可启发读者思考,同时作者还为每个问题编上序号,前后文呼应,便于读者快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阅读,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