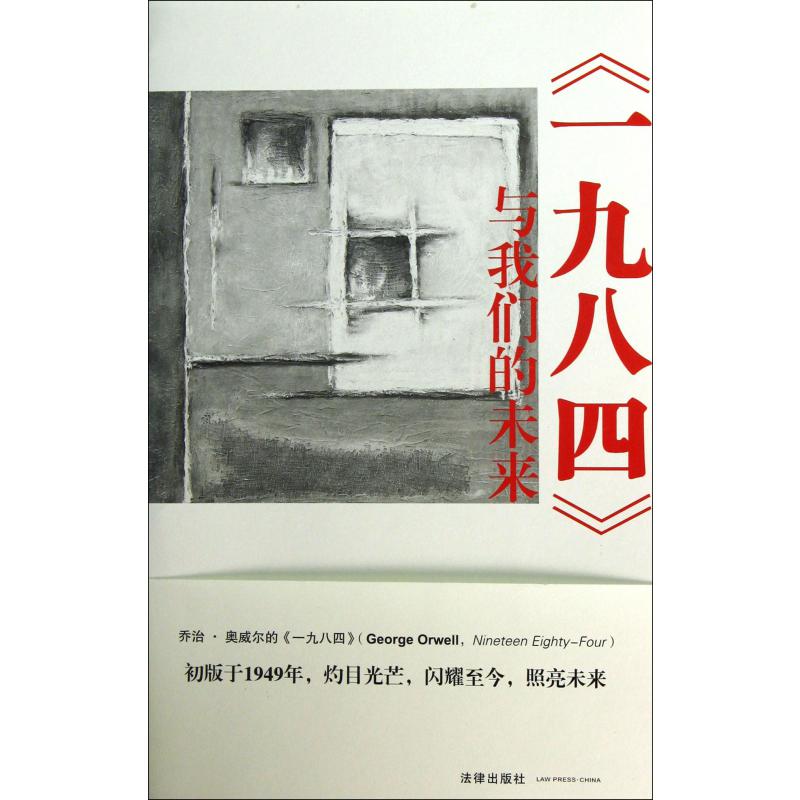
出版社: 法律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33.70
折扣购买: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ISBN: 9787511843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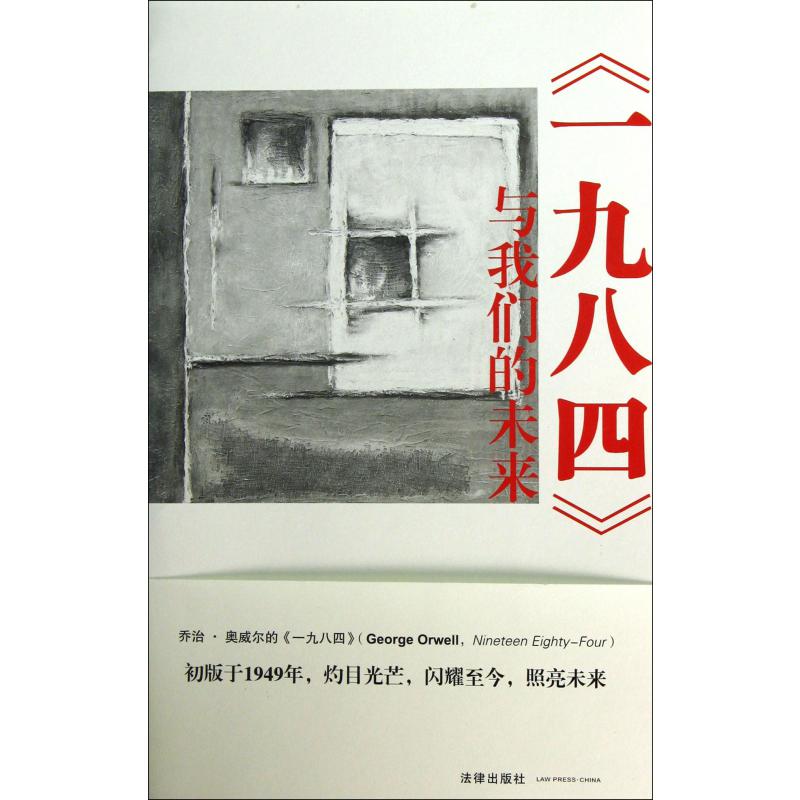
臆想让我们思索我们的视觉、触觉或其他感官当时并未感知到的那 些事物。我并没有见过那个女人踏上小桥之前的样子,但是看着她轻盈 的身影掠过小桥,我的想象不由自主地逆时间之流,向她的过去延展(这 个人从何处来?她曾经与我擦肩而过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她 呢?)同时,也有一些想象顺时间之流向她的未来延展(早在她走到桥对面 之前,我脑海中就已经浮现了小桥与对岸街面之间顺势而下的台阶)。至 于她在桥上行走的一举一动——看着她的身影,我可以感觉到描述性词 语在我的大脑中一一闪过,大脑对它们进行分类,捕捉一些,筛选掉一些, 再试试其他的一些可以描述她的词语。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我想到“有个女人正在过桥”,是大脑对现实的反应;我思索她在桥上 的行走,则是大脑对臆想的反应。你是不是觉得我把臆想的范围划得过 于宽泛了?我划出的范围比起别人已经算很小的了。你还记得我们在栗 树咖啡馆的那一夜吗?当时我们听小玛丽背诵了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 论述想象的名段。照她看,我能够想到“有个撑着阳伞的女人正在过 桥”,都有想象在起作用。当时她引用哲学家的话说:一切感知里都存在 想象,无论这感知是多么真实。 举个例子。那个过桥的女人从我身边走过时,实际上我只是断断续 续地看到了她。当时我站在桥边是为了等你。我本来一直在向桥的那一 端眺望,找寻你的身影,后来我瞥见了你,注视着你一步步向我走近。起 初我的目光锁定在你身上;接着我眼角的余光察觉到一阵反常的动静,牵 引我的目光移开了你,想瞧瞧清楚那是什么。接着,我被她吸引住了。我 的目光在你们两个之间来回移动——从她到你,从你到她。你们两个相 互走近,在桥中间碰面,后又分开,你离我越来越近,她离我越来越远。 (当时你看到我抬起了手臂,后来你还警告我说,别在公众场合这么露骨 地跟你打招呼。实际上我不是在跟你挥手,我抬起手是因为我想让她慢 些离去。) 按照休谟的说法,从现实角度来讲,我并没有全程目睹那个女人撑着 粉红色阳伞走过小桥。事实上,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看到了她过桥的片断: 此时她在桥的一个位置,下一刻在另一个位置,再下一刻、下下一刻她在 另外的位置。我看到的不过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画面,却还能确信那是一 个确实存在并且着装不凡的人,间断画面之间的空白全靠想象填补了。 这个规律更加普遍地适用于日常生活物品——我们不可能一直盯着桌椅 看而只是断断续续地、短暂地看到它们,但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是实在、 完整、持续的,这是因为有了臆想的帮助。 不过,既然我对臆想的定义比较狭隘,那么,只要你同意下面这个观 点我就心满意足了:臆想就意味着“思索”或“检验”你对某个事物的感知 是否正确——任何一个感知的形成,都是从一串否定判断开始的。要想 甄别某样东西是什么,就要判断它不是什么。虽说这种否定判断本身并 无法自动形成对事物的定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在追问“如果 某样东西不是某样东西,那它可能是什么”。这就是形成感知的一般性的 思维过程——那在天幕下撑开了的是什么?雨伞吗?不,不是雨伞,是阳 伞。那迎着光微微发亮的东西,就像沙粒;不,不像沙粒,而像奶油,呈现 出浅浅的粉红色。它有光泽,是金属吗?但它是透明的;哦,它是用丝绸 做的。你看到了吗——这些否定判断有如引路蜂,带领我们发掘出正确 认识:那位女郎撑着一把阳伞(不是雨伞),这把伞是粉色的(不是棕褐 色),是用丝绸做的(而不是金属做的)。 通常来说,我们对先导的那一连串否定判断是没有兴趣的。我们要 么不会注意到它们,要么像驱赶蚊蚋一样将其赶走,除非我们眼前的现实 包含着我们主动想要否定的因素。而一旦遇到这种因素,我们就开始从 否定的角度修正它。她打一把雨伞就好了,我当时想,打一把色调收敛的 雨伞就好了,褐色或是绿色。(那样的话她走在高高的小桥上就不会引人 注意了。)那把粉红色阳伞是用金属制成的就好了。(那样的话,她一走到 对岸,这把伞就能当盾牌保护自己了。)更多的臆想在我脑海中涌现。我 眼睛看着你走过来的一连串动作,心中却闪动着对一连串其他动作的臆 想。当你走近她时,我担心得要命,在想象中,我加快了你的步伐,好让你 们两个快点分开。(快,快从她身边走过去,那里危险。)但是,一旦你安 全 地走过去了,我又希望你能帮助她。(转身,温斯顿,看看和你擦身而过的 那人打扮成了什么样子!跟在她后面,拿件外套把她裹上,把那把不祥的 伞从她手里抽走!)但是,你一直隔着桥栏在看我,根本没注意桥上发生了 什么事情:一位绝色女郎踏着冷静的步伐走过了河,走向了死亡。 但臆想有用吗,她是为了谁而演出了这一场短暂的抗议?我的大脑 热情炮制出的臆想,并没有改变她的悲惨命运。(不过,要是我跑得快,或 者你懂心电感应,我们两个指不定谁就能及时帮到她了——你看,问题在 于我们臆想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即便如此,臆想还是会使我们从两个方 面受益。它本身蕴含着自由。它使我们不囿于已然发生的事实,而去自 由描绘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撑着丝质阳伞不会出事——可能因 为河对岸不会有士兵开枪向你射击,也可能因为有个朋友在你没走到河 对岸前,就把阳伞从你手中抢走了。同时,它使我们得以置身事外片刻, 借此更加透彻地看穿事实。它使我们隐约意识到她为何这么勇敢——她 本不必这样做,完全可以不选择粉红色,完全可以不高高擎起她的伞,完 全可以不在阳光这么灿烂的一天出门,这样阳光就不会在伞沿上闪得这 么惹眼——她的勇气,全然来自于她对权威的藐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所以我在观察她的时候,就暗自给她取了一个名 字。你能猜到我叫她什么吗?奥黛特?西蒙娜?保利娜?这些名字都很 配她梦一般的身姿。但你错了,我叫她波吕克塞娜,这是一个年轻特洛伊 女孩的名字,希腊人决定用她来充当祭祀阿喀琉斯的牺牲品。她同意牺 牲,却拒绝被拖去祭坛:“解开我的手,我自愿赴死。”那个撑阳伞的女子 , 当她走在小桥上,走在她自己的一米阳光里时,她一定想到了前人的一句 话:“现在属于我的光明/存在于此刻与/彼刻的杀戮之间。” 在大洋国,这个臆想的冲动被破坏殆尽的国度,我们几乎从不臆想。 即使偶涉,也是在极端不幸的情况下,臆想相反的情况。但在其他国度, 在那些人们生命不受威胁、穿戴丝绸不受惩罚的地方,人们十分珍视臆 想,也很容易产生臆想。一顶帽子的掉落都可能引起臆想。在那样的世 界里,即使并非什么人有生命危险,甚至并非什么人感到不悦,只要我不 喜欢某种颜色,这一点本身就可能让我想到另一种颜色——当然,如果不 考虑我看到一个不太喜欢的颜色这件事本身可能就是一点小小不悦的 话。比如,看到一件粉红色裙子,我可能会觉得粉色不如薰衣草的浅紫色 好看。“这条裙子并不是浅紫色”这个状态,可能让我感到讨厌,并足以促 使我在想象中用浅紫色替换粉红色。你抱怨美学界的大人物们都道德败 坏,只图享乐,这样说不假;但是他们保持着灵活的头脑,随时准备着,一 有需要就可以去做很重要的工作。装饰品在视觉上是独立于它所装饰之 物的,所以它是臆想的现实替代品。装饰品只要存在,就会不断地引出问 题:你喜欢吗?你百分百喜欢吗?你希望对它做出改变吗? 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半身心地爱上了那个在我们的窗户下洗衣 的女人了吧?(同时全身心地爱上了那个无论你什么时候转过身来,要么 没穿衣服,要么正在穿衣服的女人?)在大洋国统治的最初几年,统治者觉 得只要杜绝人们写作和绘画用的纸张和画布,就可以遏制臆想的生存空 间。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人们在日常梳妆的时候,还是会想法子扮靓自 己,其本质与写作和绘画并无不同。因此,大洋国竭力控制装饰品的生存 空间。他们给了我一条红腰带,每天必须系着,就连应该在哪个地方打结 都有硬性规定。他们把所有能让人们自行改变外观的东西都杜绝了—— 从肥皂、衬衫、亚麻织品、蕾丝花边到发卡(可以让人变得如此美丽,如同 有天使在发卡尖上舞蹈)、剃须刀片(可以让你脸部的轮廓更加清晰,还可 以让我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清晰地刻在这里)。 P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