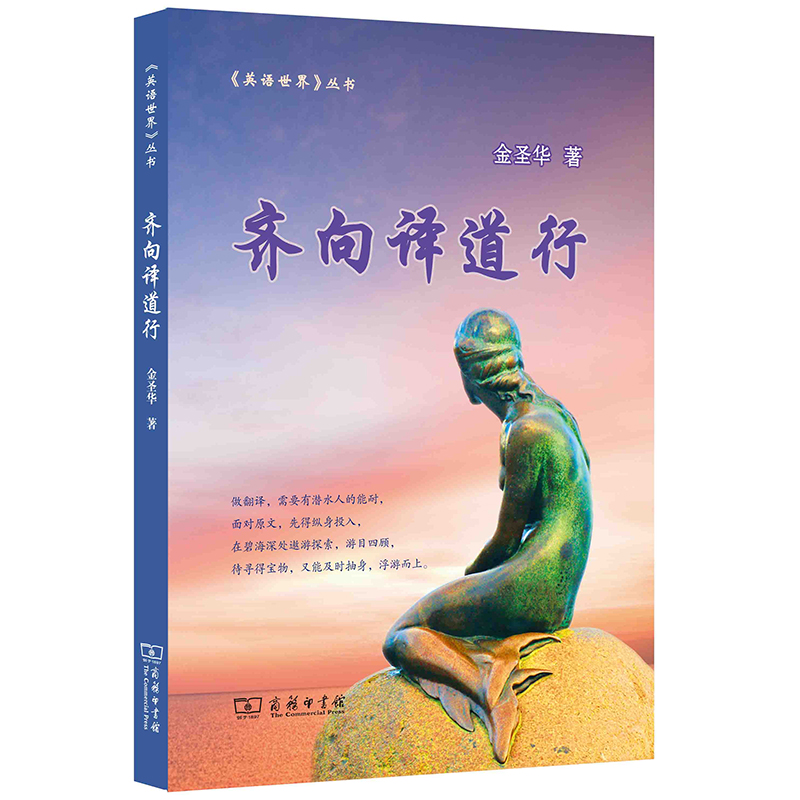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56.25
折扣购买: 齐向译道行/英语世界丛书
ISBN: 9787100075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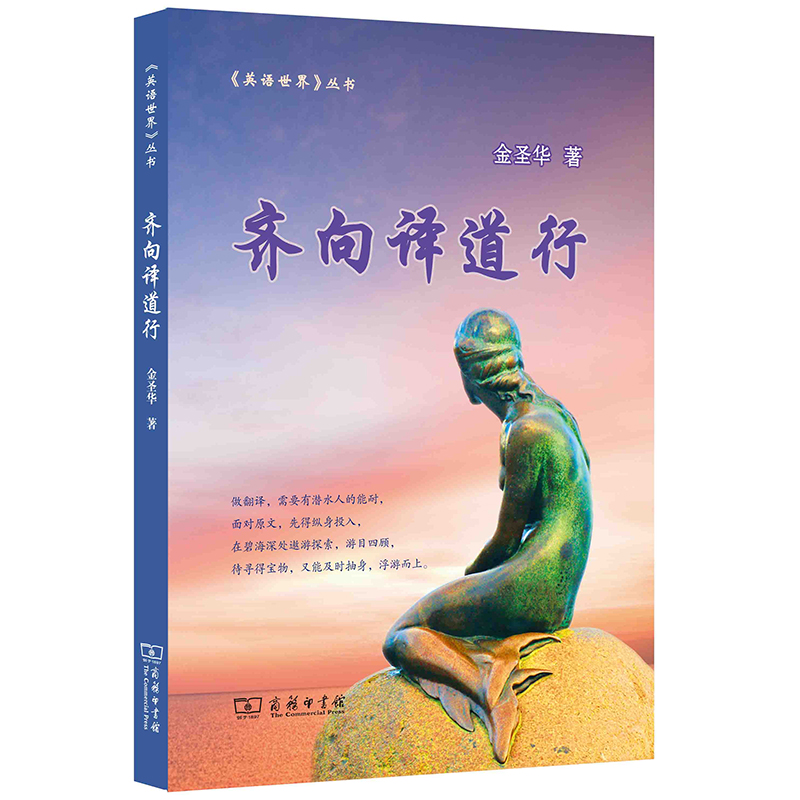
金圣华教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学院,后又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及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1997年6月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O.B.E.(英帝国官佐)勋衔。曾编撰多本著作,如《傅雷与他的世界》、《认识翻译真面目》、《江声浩荡话傅雷》等;并翻译多部文学作品,如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麦克勒丝的《小酒馆的悲歌》、布迈恪的《彩梦世界》,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中译等,并出版多本散文集,如《树有千千花》、《披着蝶衣的蜜蜂》、《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等。
十三 从春天说起 对于夏的描绘,由于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颇多分歧。英语中有关的诗文,最常引用的可能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Sonnet 18)起始的两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这首诗已经由不少名家译成中文,也有很多翻译家提出讨论,此处不赘。但是为什么“a summer’day”引起这么多的话题? 主要原因是对英国读者来说,夏天可爱温煦,风和日丽,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夏日炎炎,天气暑热,在骄阳肆虐之下,只有汗流浃背的可能,哪里还有“lovely and temperate”的感觉呢? 因此不少译家必须在译文中作出调整,既不对原文作者背逆不忠,也不使译文读者疑惑难明,这权衡轻重的步骤,就是译者的功力所在。 当然,对于夏的感觉,即使英伦的作家,也未必人人都跟莎翁相同,灼人的夏、干旱的夏、酷热的夏等并非罕见,因此夏天可以“splendid”,也可以“scorching”,中文里涉及夏的词汇除了“夏日、夏天、夏季”之外,当然很多:例如“初夏,盛夏、仲夏、炎夏、酷夏、立夏、湿夏、朱夏、孟夏、暮夏、隆夏、苦夏、蒸夏、炎暑、酷暑、隆暑、烈暑、残暑、伏暑,残夏、紧暑、三伏天、夏至、夏临”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余光中教授论翻译,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字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翻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这句话说得十分有道理。试想想,假如在创作或翻译时,我们只知道以欧化语、舶来品充场面,而不懂得运用千百年来含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啻把自家的宝物抛出去,把别人的垃圾捡进来。这一进一出、一弃一用之间,所谓的现代汉语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不觉间显得苍白无力、面目可憎了。译文体之所以肆虐为患,其实是由于许多死译劣译充斥坊间直接造成的。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是一项原则,真要实行起来,若没有一些国学根底,也并非易事。学生翻译时,时常不知文白调配与文白夹杂的分别。调配得当,固然可“水乳交融”,夹杂失当,却显得“水火不容”。再以上述的例子为例,能善用文、白综合语法的译者,译来老练浑成:“观德莱顿之一页,犹如田野一方,高低错落,自然天成,其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更使其姿态万千。蒲柏之则似碧草一坪,柔如鹅绒,其平整有序,刀割磙压。”不善用综合语法的译者,则译成:“德莱顿的作品是一片天然的土地……而蒲柏的作品就像一片刚被镰刀割齐又被碾轧机轧平了的天鹅绒一般的草地。”后者译文中“被被不绝”、“的的不休”的长句,完全是因为翻译时受外文语法操控,亦步亦趋所致。为什么不尝试摆脱牵制,向母语求援呢? 三十七 险中求胜、窄处回旋 常有人说,创作与翻译不同,创作如天马行空,万里穹苍,无边无疆,作者大可任意翱翔,尽情挥洒;翻译恰似戴着镣铐起舞,一举一动都受制于人,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翻译的确像戴着镣铐起舞。这镣铐就是原文的句式、语法、词汇、字义,文化的底蕴,历史的积淀,这一切都各有分量,加在一起,变得沉甸甸,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因此,翻译是一桩吃力的工作,不管新手老手,要认真慎重地译一篇文章、一本著作,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这镣铐虽不能解脱,但通过学习、通过锻炼、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与经年累月的浸淫,竟也可以变得轻、变得巧,变得不再磨人、不再沉重。行军讲求绝处逢生,险中求胜;翻译,又何尝不可窄处起舞,回旋自如呢? …… 除了文言句法、词汇,有时候也应借助一些新鲜活泼的口语及习用语。翻译时,不同的文类,需用不同的表现方式,戴着镣铐跳芭蕾舞或HipHop,自有不同的跳法,不可一概而论。譬如说,原文用字浅显,不涉典故,但由于词义笼统含糊,这又如何是好?有位同学选译Mimi Chan’ All The King’s Women。原文涉及一名小女孩,其中有一句为:“The little girl, Ying, was so small.”译者翻为“英是个小女孩,年纪很小”,评论者认为“small”应指“个子很小”。倘若翻查字典,“small”既可指“年纪小”,又可指“个子小”,那么,此处到底该怎么译? 作者为什么先用“little”,后用“small”? 按说,小英应为年纪又小、个子又小,但翻译时,译者往往需化虚为实,审慎落笔,因此,这么简单的英文原文,也会造成困难。经过思量,乃建议学生译为“小女孩英,这么个小不点儿”,因为在口语中,“小不点儿”既可指“年纪”,又可指“个子”,译来既妥帖又传神。 做翻译,需要有潜水人的能耐, 面对原文,先得纵身投入, 在碧海深处遨游探索,游目四顾, 待寻得宝物,又能及时抽身,浮游而上。 本书深入研讨了文学翻译中精微细致的技巧,采取不同于大学课堂高头讲章的随笔形式,将翻译心得娓娓道来。每篇章虽短,却各有要点,对一些翻译问题的总结也细致入微。文字优美生动,内容深入浅出,表现了作者的丰厚学养和深厚功力。对于翻译初学者而言,这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书。即便是一个与翻译学全然陌生的人,也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学术随笔来读。正如金教授所说,“翻译好比做人,译道恰似人生”,唯有不惧译途之艰辛,才能收获奇遇,在周转回旋中参透译事之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