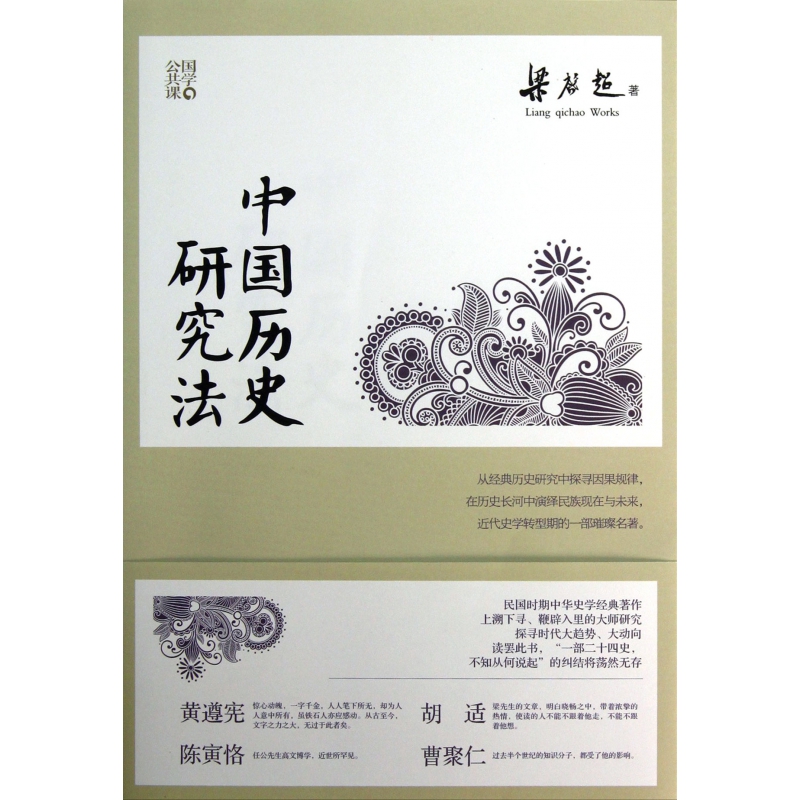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华侨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18.00
折扣购买: 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学公共课)
ISBN: 9787511334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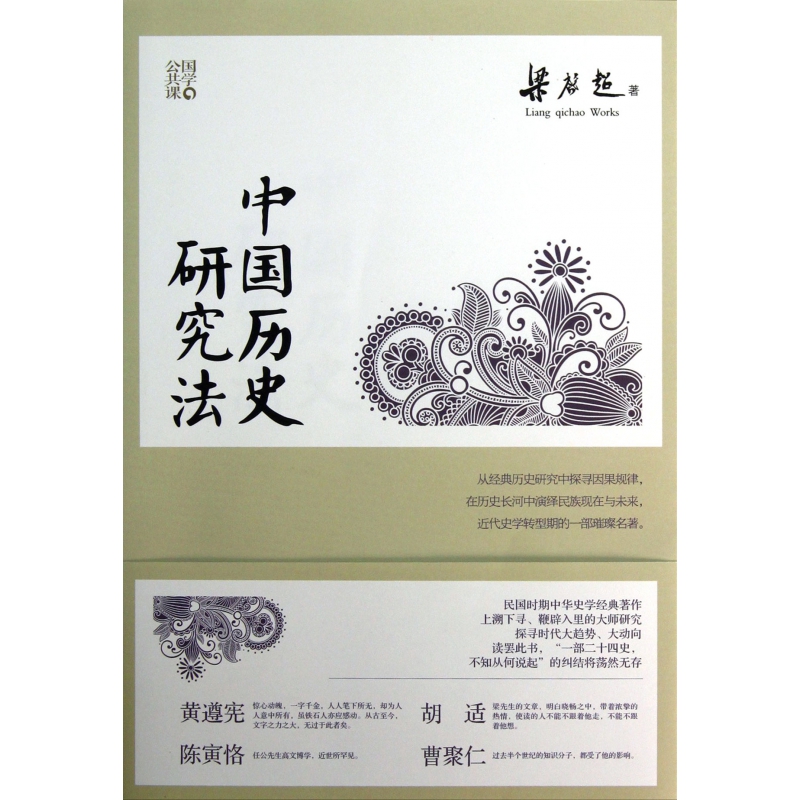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被时人称为舆论界的骄子。他还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纵笔所至不拘束,而笔端又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代表作《少年中国说》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 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 ,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 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 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 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 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 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 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 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 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 ,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 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 ,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 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 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 。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 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馀诸史目的略同, 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 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 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 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 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 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 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 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 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 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 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 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 ,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 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日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 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 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 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 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 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 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 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 ,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 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 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 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 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干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 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 ”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 ,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 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 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 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 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 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 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 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 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 科,日“年代学”,日“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 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 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 馀。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 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 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 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 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 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 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 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 、《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 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 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 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 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 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 。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 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 ,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 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 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 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 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 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 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 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 ,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 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 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 ,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 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P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