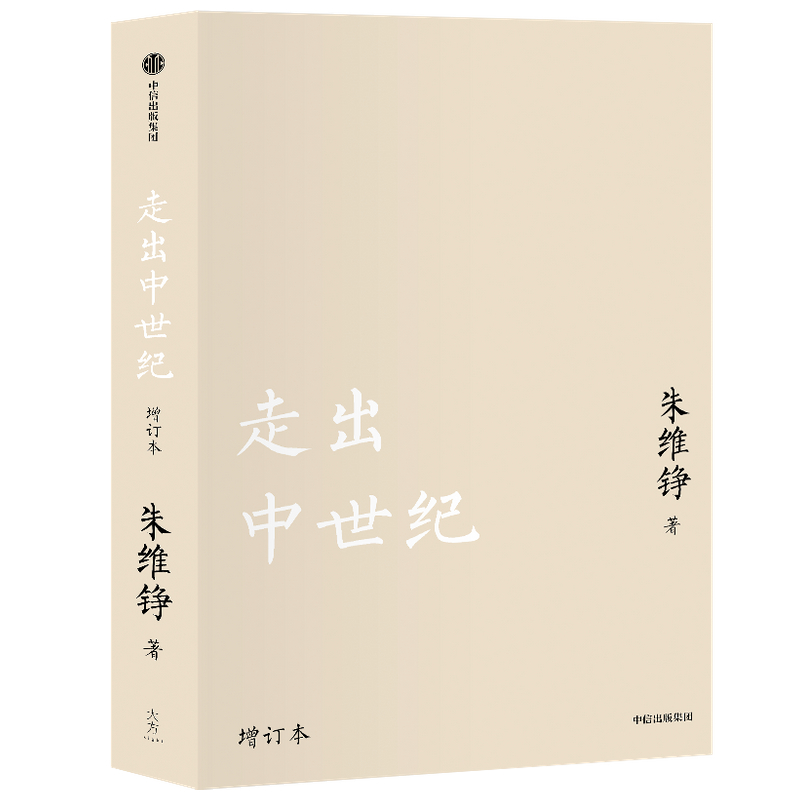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70
折扣购买: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ISBN: 9787508690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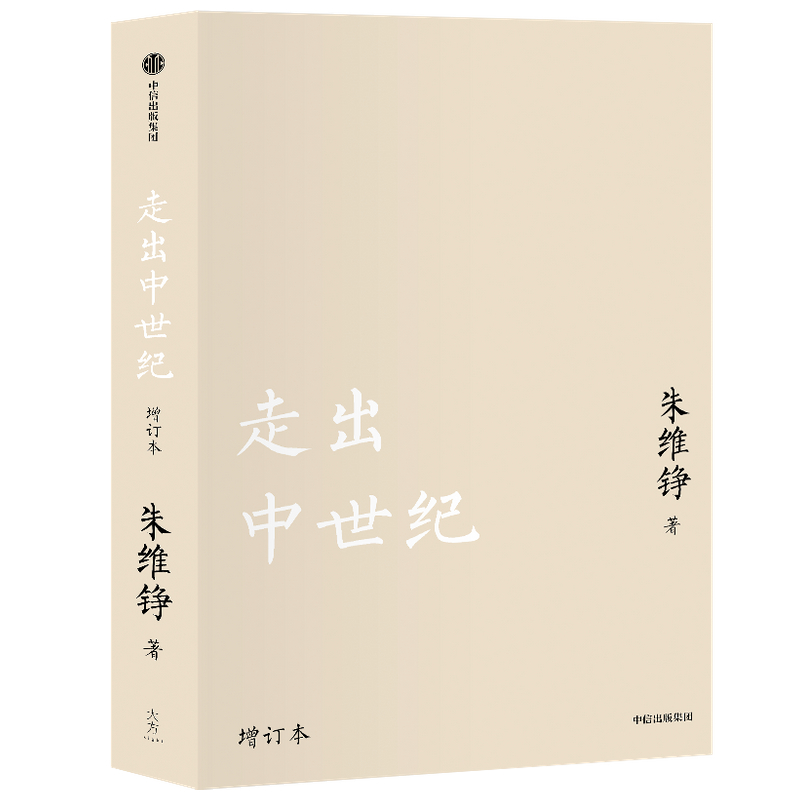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从教52年。200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眼光独到,笔锋犀利,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治学范围涵盖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已刊论文及讲演录二百余篇,著作十余种,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种,《走出中世纪》等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我们不知道恩格斯在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两千年前中国那个短命的秦朝的历史,可是这话确实好像在评论秦朝统一六国以后的作为。秦始皇从灭韩到灭齐,用了不过十年的工夫,在古代世界军事史上也属于辉煌的业绩。但他能将六国变成过去式的地理名称,甚至能纵容他的将军把几十万俘虏在一夜间从肉体上消灭干净,却没有能力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消灭几百年间形成的唤作诸子争鸣的文化氛围。善于利用君主心理以击倒竞争对手的李斯,借机向皇帝提出了所谓“安宁之术”,即用禁毁图书、控制教育等手段,“使天下无异意”。秦朝虽然很快覆亡,但它开创的中世纪文化的一大原则,就是想方设法防民之口,乃至不容在头脑中异想天开,却被中世纪的统治者竞相采用。从汉晋到明清,列朝法典屡有修订,历代法网也有疏密,但以言治罪、论心定罪的相应律令名例,则从来没有受到忽视或舍弃。不信,请看那繁密的“大清律”以及更加琐细得可怕的所谓“例”。 不错,这种中世纪的独特安宁术,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变得不那么粗野了,表征就是儒术取代了法术,在文化政策上引出一连串反向变异。比如说变不准挟书为鼓励读书,只要读的是君王批准的圣经贤传及其官方诠释。比如说变以吏为师为以儒为师,只要所谓的儒者通过政府的审查或考试被认作具备了教官的资格。比如说变禁止论政为允许谏诤,只要谏诤者获得奉旨说话的特权并且保证“思不出其位”。诸如此类,应该说替思想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某种蹊径。但中世纪文化史不是表明,那非但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还随着儒术变得愈来愈精致而愈来愈将思想文化导向绝处吗?因而,那种变异的相反取向,无非是采用另一种策略贯彻“使天下无异意”的文化原则,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殊途同归。早在这种变异发生的初期,在把儒术提高到统治者格外尊奉的安宁术的过程中,公孙弘和董仲舒,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侧面,对此做出过重大贡献。那贡献,用司马迁、班固都说过的一句话,便可概括,就是“以儒术缘饰吏事”。行事不妨摭拾秦律,包括号称苛法的“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说话则必须奉天法古,就像董仲舒用《春秋》决狱那样。 2.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犹如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的躯体上面的一颗脑袋。从秦朝末年到清朝中叶,二千年间,它曾经屡次被造反的农民所打烂,也曾经一再被入侵的“蛮族”所尝试置换。因此而造成的周期性无政府状态,或者导致频发性前封建体制的复归,在当时都曾使忧国之士吃惊与呻吟,似乎固有的脑袋从此失落。岂知它却好比《西游记》里那个牛魔王的脑袋,即使一再被割掉,仍然会从腔子里再长出一颗来。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既不乏深受君主专制迫害的农民奋起革命并取得或局部取得成功的例证,也不乏保留古老民主习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维护自己体制的例证,但还找不到那样的例证,就是受害者没有采取害己者的政体,征服者不曾接过被征服者的制度。乞丐僧人朱元璋造反成功,厉行君主专制远胜于宋元王朝;三家村小学教师洪秀全率领农民手工业者起来革清朝的命,才取得半壁江山,便很快忘记了自己信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在石头城里用新名称恢复旧制度。至于征服者顽强保护本族政治文化体制,最终却把被自己所取代的胜朝体制当作完美的模式,例证也毋需远举,清朝便是。可见,除非中世纪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也即旧躯体已经或是濒临死亡,否则君主专制政体,也许会被整容,也许会有局部更新,却不可能完全的革除旧貌,换成新颜。 3. 谁若留心晚明学术史的全貌,谁就不会不注意一个历史现象,即前述利玛窦的传教路线,恰与王学由萌生到盛行的空间轨迹重合。 …… 从1595年6月到1598年6月,利玛窦在南昌生活了三年。他或许是那个世纪现身南昌的头一个欧洲人,没想到并未受到预期的敌视,相反得到各类人士的善待。他受宠若惊,苦苦思索原因,于是关于江西知识阶层乃至达官贵人何以普遍地待他友善的分析,便成了这三年他寄往澳门和罗马的修会当局及师友的信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洋人居然通经书?想学点金术?欲知欧式钟表的秘密?爱听西洋数学的介绍?真想聆听“得救的福音”?如此等等,他都想到了,唯独漏举这里是王学的真正故乡。 尽管利玛窦并不真正懂得人文环境和思想传统的互动关系,却不妨碍他和晚明入华的耶稣会士,在某种占优势的思想传统所笼罩的特定的人文环境中间,享有谈论异说或宗教信念的相对自由。晚明王学宗派林立,竞相标新立异,无疑与从陈白沙到王阳明都宣扬学术贵“自得”是一脉相承的。所谓自得,强调过度,势必如章太炎在清末所讥,讳言读书,乃至自我作古,割断历史传统。然而在经历了嘉靖朝长达四十五年的君主独裁制造的思想高压的岁月之后,提倡学贵自得等于吁求学术独立,要突破腐败统治的思想牢笼,当然也意味着向中世纪专制体制争自由。按照逻辑,过度估计个人学说的独创性,必定导致对于《孟子》所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命题的再诠释,如王阳明承认“涂之人皆可为禹”,同样导致承认陆九渊关于古今中外都可出圣人的推论,即凡圣人都“同此心同此理”,属于普遍真理。利玛窦入华,正逢王学解禁,正值“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理论风行一时,因而他传播的欧洲学说,被王学思潮最旺的南昌学者士人,当作来自西海古圣前修发现的新道理,是不奇怪的。 看来利玛窦很满意南昌的人文环境,不止一次地写道:“我感到此地真是值得致力传教的好地方”;“我相信在这里一年的收获,较过去整个十余年在广东获得的还多”;“假使我能在南昌建立一座会院,我相信在这里一年的收获,将超过我十四年在广东所有的总和”。 1. 随想录式的著述风格——朱维铮先生擅长用大笔写小书,他的这部代表作并非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而是体例、长短各一的历史札记,轻松易读,也符合他对史学严谨负责的态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话短说,言尽为止”。 2. 诠释学的方法——朱维铮先生解读史料的能力强,能从旧史料中读出差异与新意。擅长“证伪”,将可信的常识证成待解的疑团。 3. 启蒙的立场——朱维铮先生研究的是经学史而不是经学,不再把经学当作信仰的宗教、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他反思90年代风起云涌的保守主义,为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风降温,激活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 4.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朱维铮先生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避免以论代史,用预制框架套裁客观事实。 5. 独立自由的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的一生都在为“纯学术研究”正名。“钻故纸堆”并不意味着忽视现实问题,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史家的冷眼和士人的热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