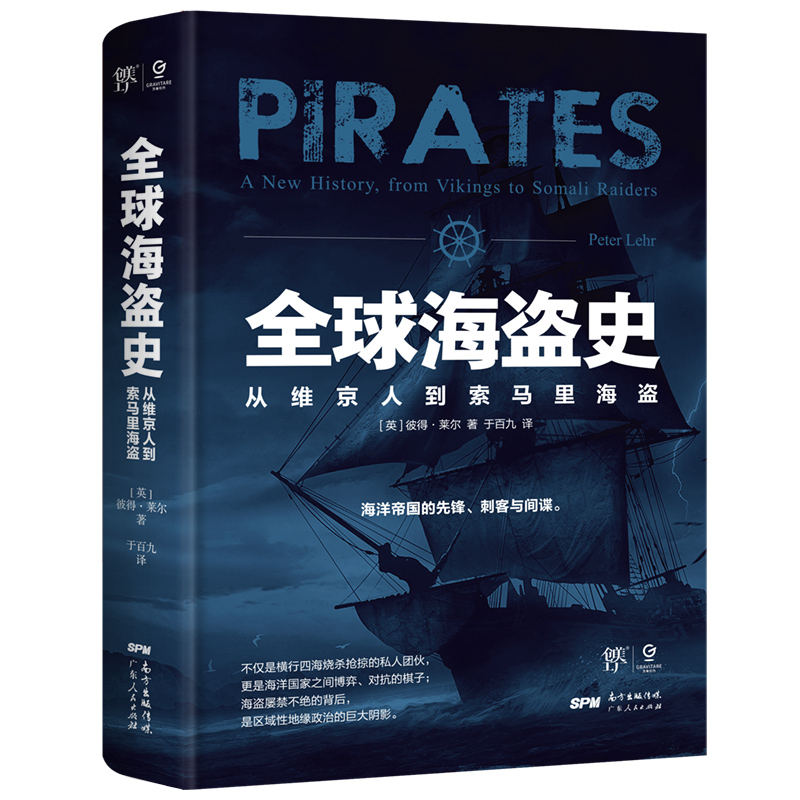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全球海盗史
ISBN: 9787218152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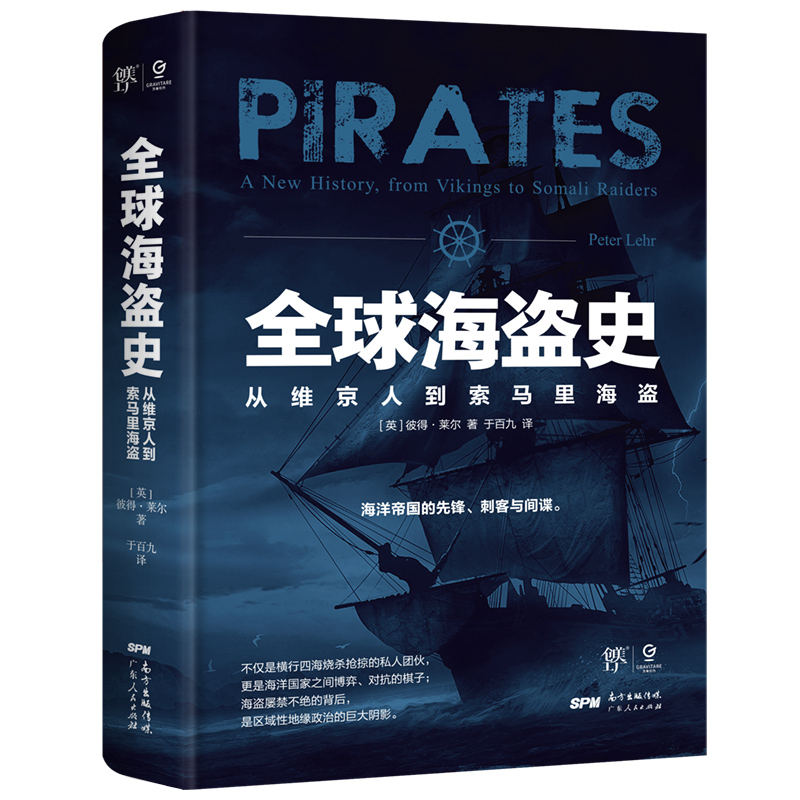
彼得·莱尔,德鲁斯大学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讲师,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著有《反恐怖主义技术》,编有《海上暴力:全球恐怖主义时代的海盗》。
入伙贼船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成为海盗或私掠者,决心靠海上劫掠为生?浪漫的好莱坞大片和小说总是会掩盖一个丑陋的事实,即当海盗是一个(在世界上很多水域仍然是)非常危险的职业。在过去,人们选择这个职业可能是为了快速致富。但更有可能的结局是溺亡、饿死,抑或死于坏血病、疟疾、瘟疫或者任何一种当时尚未命名的外来疾病;也可能因事故或战斗而终生残疾;也可能战死,或者被各种可怕且相当难以忍受的方式折磨致死;也可能被政府处决,或者干脆被扔到监狱里等死。所以,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海盗作为职业,并不一定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也不一定是出自对冒险的热爱。 下决心当海盗,通常由两种力量之一驱动:一种是对现实的不满,比如贫困无助、失业、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对未来几乎不抱希望;另一种则是贪婪和快钱的诱惑。畏罪潜逃则是另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大海一直是社会上那些违法犯罪行为的避难所。”1这些要素的实际影响,并不依赖于大的地区因素,而是跟次级区域乃至于当地的具体环境紧密相关,这些具体环境可能随时间发生巨大变动。 中世纪晚期,也就是1250—1500年,在地中海地区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区域,为那些有上进心的人——尤其是技艺熟练的手工匠人——提供了很多完全合法的成功机会。但是,人口增长同样会带来失业率上升,那些较贫困的局部地区则会愈发贫穷,原因在于各个海洋强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劫掠和反劫掠,而这些势力又依赖于私掠者(即“持证劫掠”的私掠海盗)和“无证劫掠”的海盗。在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势力范围内,存在着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老牌海洋强国,它们的繁荣得益于诸多港口之间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包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港口(如亚历山大)、黑海沿岸的港口(如卡法 )。丝绸、香料、瓷器、宝石、黄金、白银、毛皮和奴隶等高价值的货物,让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而拜占庭和亚历山大的商人也没少赚。如果生活在这些繁荣的港口城市的市民想要去当海盗,那么多半是贪欲作祟,私掠者也是如此。显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从事这样的高危行业,这些人可能失去的东西最少,可能获得的利益却最多。以港口城市贝贾亚(Béja?a,位于阿尔及利亚)和特拉帕尼(Trapani,位于西西里岛)为例,“出身平凡的人”比如工人、小商贩或工匠、渔民以及海员会把出海劫掠当作兼职。2至于那些居住在散布于航海路线上的小岛上艰难度日的渔民和农民,他们肯定早就对满载的过路商船垂涎三尺了。经济的发展通常无法惠及这些地区,而且私掠者在猎捕奴隶的过程中也经常造成破坏,同时还会拿走任何能赚钱的东西。在怨愤和贪婪的共同作用下,上述的一些地方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知名的海盗窝点——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延续到了19世纪。 在北欧海域,艰苦的生活条件同样是组织松散的海盗和私掠舰队诞生的核心原因。私掠舰队一开始被称为“粮食兄弟会”(Victual Brothers),后来叫作“均分者”(Likedeelers),活跃于14世纪最后十年和15世纪早期的波罗的海及北海地区。在这片区域,持续的海战给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而压迫式的封建土地秩序使得农民处于严苛的、入侵式的控制之下。13—14世纪,大量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工人移居城市,希望能在城里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却发现,在相对单一的城市生活中,他们的境遇愈发悲惨。条顿骑士团国(State of the Teutonic Order)的情况尤其如此,这是一个由天主教军事组织建立的国家,疆域包括今天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和瑞典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该组织参与了对抗非基督教部族王国和公国的十字军东征,直到15世纪初期。 海盗活动在波罗的海水域早已司空见惯,其形成原因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同:这里密集的海上交通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而沿海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又导致海洋警务无法有效进行。例如,在1158年,苦于频繁的海盗侵袭,丹麦沿海地区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西兰岛(Zealand)的居民纷纷逃往内陆地区,留下了日渐荒芜和无人看守的土地:“到处都是荒芜一片。武器和要塞也靠不住。”314世纪最后十年,梅克伦堡的约翰公爵在与丹麦的玛格丽特女王交战期间,向所有站在己方的人都发放了私掠许可证。此举大大放松了限制,使得无组织的零散海盗发展成有组织的庞大舰队。梅克伦堡与丹麦的战争主要在海上,这就需要建造新的战船,也需要新的水手。战争会带来大量抢劫掠夺的机会,于是出身三教九流的冒险者和亡命徒(其中以北德意志人为主)纷纷聚集在梅克伦堡的港口,急切地应征。《德特马编年史》(Detmar Chronicle)这样描述他们: 在这一年[即1392年] ,一帮难以管束的臣民,也就是来自各个城镇的市民、官员和农民聚集在一起,自称“粮食兄弟会”。他们表示,将要讨伐丹麦女王,以解救被她囚禁的瑞典国王。此外,他们不会俘虏或劫掠任何人,反而会支持那些用物资和援助来参与对抗丹麦女王的人[来自梅克伦堡]。 粮食兄弟会并没有遵守这一承诺,反而威胁到了“整片海域和所有商人,无论是敌是友”4。 所以说,粮食兄弟会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均分者”跟其他大型的有组织的海盗集团一样,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鉴于其团伙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没人留下回忆录之类的记录,因此,到底是贪婪还是怨愤导致这帮人走上了海洋抢劫之路,还有待讨论。不过这两个因素很可能在刺激那些来自汉萨同盟大城市的众多成员身上发挥了作用。他们多半意识到,梅克伦堡公爵对私掠者的召唤太过于诱人了——这是一个摆脱赤贫、大发横财的好机会;就算是死了,起码也算是为更好的生活争取过。5对于现有的水手来说,加入粮食兄弟会则更有意义:尽管梅克伦堡的私掠合约包括了“没有劫掠,就没有报酬”的条款,但是通过掠夺致富的好机会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如果船长决定要加入海盗兄弟会,船员们甚至不需要换别的船。商人与私掠者、海盗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的船只配备的人员更优秀、武装程度更高。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情况,海上强盗联盟的称号就特别能说明他们的特征。一般认为,“粮食兄弟会”这个名字来自该集团受雇为私掠者时负责的一项任务:1390年,这个私掠者兄弟会受命为斯德哥尔摩饥困的民众提供补给——或者说“供粮”(victualising)——该城被丹麦敌人切断了补给。6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粮食兄弟会”这个名字单纯是指他们自给自足的状态。7“兄弟”或者“兄弟会”暗示了成员之间可能不平等但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特征在“均分者”这一名称(Likedeelers来自中古低地德语)中变得更加突出,这个称呼出现在1398年左右的德语文献中,意为“平均分配的人”。在等级森严,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社会地位的时代,不论高低贵贱、战利品平均分配的概念本身便是对政治精英(贵族、教会和强大的汉萨商人)的一种挑战。 有趣的是,在中世纪那些决心走上海盗或者私掠道路的人当中,不仅仅有被压迫的阶层。海盗和私掠者的生活甚至有可能诱惑一些贵族——并且通常出自非常相似的原因:为了逃避残酷命运给他们带来的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当然了,这里说的贫穷只是相对而言,很多贵族可以说是被冒险精神而非其他原因带到大海上的。但是,也有很多贵族出身的人被迫当了海盗或者私掠者。例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各个城邦之间,甚至不同派系之间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导致许多名门望族不得不离开家乡,踏上逃亡之路。他们“寻求通过从事海上袭掠和路上抢劫的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更准确地说,多半是为了生存)。1325年左右,许多来自热那亚的吉伯林(Ghibelline)8战船攻击船队、进行海上突袭和抢劫”9。1464年,就连热那亚的公爵兼大主教保罗·弗雷戈索(Paolo Fregoso)都当了海盗——在当时还算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海盗——此前他被政敌驱逐出城。10在这个阶段,意大利的流亡豪门并不是唯一处境艰难的贵族。1302年,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平让加泰罗尼亚的骑士们纷纷失业,陷入窘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便集结到一个叫罗赫尔·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的人旗下,此人曾是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的一名军士,因涉嫌行为失当而被逐出骑士团,当了海盗。对于这项职业,他有着丰富的经验。从8岁开始,他便在圣殿骑士团的战船上担任见习骑士,其间屡遭海上突袭。在14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职业雇佣兵以加泰罗尼亚大佣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的名头,活跃在东地中海,干着私掠或海盗——取决于他们是为了某个领主而战还是纯粹为了他们自己——的营生。11 对于14世纪末的粮食兄弟会和波罗的海而言,情况略有不同。很多低阶贵族尽管维持着表面光鲜和贵族排场,实则已经陷入了“不幸的贫穷”(infausta paupertas)状态。12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依赖于名下土地的收入,当农产品价格跌入谷底时,他们极易受到频繁发生的农业危机的影响。作为动荡的战乱时期的典型产物,这些贵族至少还拥有一项适销对路的技能:在频繁的大小战争中磨炼出来的久经考验的战斗能力。不仅如此,由于其悲惨处境,他们通常会认为抢劫和掠夺只是“小恶”“微不足道的罪过”,并不觉得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当时的一句谚语证实了这一点:“闲游也好,抢劫也罢,都无伤大雅;世上最良善的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ruten,roven,det en is gheyen schande,dat doint die besten von dem lande)。”13于是,把陆地上抢劫的行为延伸到海上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当然了,这里又有一点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决定加入海盗集团的贵族都会担任首领。他们依靠微薄的财产,购置一艘大船,配备上武器,带上自己身经百战的随从。他们不无理由地希望能靠着一两次成功的突袭收回成本。在其他比较穷的贵族当中,有一些仍可凭借出色的战斗技巧和领导能力攀升到海盗集团的领导层,无须事先自掏腰包买船。有两位托钵修会出身的僧侣便是这样,他们在粮食兄弟会中担任高层要职。14 这两位僧侣加入海盗集团的原因无从知晓。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不是最早成为海盗的修士。15“修士”厄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又号“黑修士”,原名厄斯塔斯·布斯凯(Eustace Bousquet),1170年左右生于法国布洛涅 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博迪安(Bauduin)是这片沿海地区的一位高级男爵,而厄斯塔斯似乎在骑士素养和航海技术两方面都受过很好的训练;日后作为私掠者和海盗所取得的出众战绩表明,他早年间很可能在地中海当过私掠海盗。16尚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进入本笃会修道院成为一名僧侣;但他离开教会的原因倒是比较明确:除了某些涉嫌行为不良的流言外,他还试图为父亲报仇,他父亲被另一名贵族所杀。在布洛涅一带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亡命生涯之后,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地中海做私掠海盗经验。大约在1204年,他加入了英格兰的约翰王麾下成为一名私掠者,当时约翰王正在跟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进行一场持久战。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厄斯塔斯不仅袭击法国船只,还攻击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沿海地区。他将萨克岛(island of Sark)变成了一处半独立的海盗据点,惹恼了附近的英格兰港口黑斯廷斯(Hastings)、新罗姆尼(New Romney)、海斯(Hythe)、多佛(Dover)和桑威奇(Sandwich),这五座港口亦称“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也饱受厄斯塔斯的劫掠。当1212—1213年英格兰宫廷开始反对他时,厄斯塔斯迅速改换门庭,回到了法国阵营,转而袭击英格兰船只、攻击英格兰沿海地区。最终,他在1217年8月24日的桑威奇战役中丧命。英格兰水手投撒石灰粉,弄瞎了法国士兵的眼睛,成功登上了厄斯塔斯的战船:“他们跳上了厄斯塔斯的船,残忍地结果了他的手下。所有的贵族都被俘虏,‘修士’厄斯塔斯被杀。他的头被砍了下来,战斗旋即结束。”17 违背庄严的誓约投身海盗事业的,不只是个别基督教修士: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还发现了同样走上这条路的古怪佛教僧侣。例如,徐海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博学僧人,在杭州城外著名的虎跑寺修行多年,过着平静的生活。18但是,1556年,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离开寺院加入倭寇——这是15世纪40年代至16世纪60年代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集团。19他通晓典仪、诵经和算卦,这给他带来不少好处,为他赢得了“船员们的忠诚,他们称他为‘天差平海大将军’”。20但是,就像加入海盗的北海及波罗的海的基督教僧侣一样,徐海的情况也是特例,而非普遍现象:倭寇主要从日本、中国和马来地区招募新人,他们要么因为贪婪,要么因为怨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是曾经服役过正规海军舰船的经验丰富的中国水手。促使海盗数量激增的原因在于政府通过了对海洋贸易的严格约束法令,甚至彻底“海禁”,以及遣散强大的明朝远洋舰队——这支舰队曾经在郑和的率领下,于1405—1433年多次游历印度洋海域。 中国海事政策的这一突然变化导致数千名水手失去生计,他们只能绝望地寻找新的出路。很多商人选择通过转投海盗来继续他们已经变得非法的贸易活动——要么组织突袭,主动出击;要么抵御劫掠,被动防守。这些商人海盗中最有权势的汪直 ,在当海盗之前曾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富裕盐商。在日本封建领主的庇护下,他在九州设立据点, 并在那里掌控他飞速发展的海盗帝国,但从不主动参与任何劫掠行动。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从受的商人变为令人恐惧的商人海盗,并非出于自愿:明朝的海禁摧毁了他的海上贸易事业。21他别无选择。 神的旨意 如果当海盗不会留下什么社会污点,那么这条路会容易走得多。在某些海洋文明里——比如从中世纪早期的8世纪起就肆虐不列颠群岛、爱尔兰和欧洲大陆沿海地区的维京人;再比如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差不多同时期的罗越人(Orang Laut,直译为“海洋之民”),他们经常袭掠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这些掠夺者被视为高贵的勇士,值得被崇敬和尊重。22在这些文明中,参与海盗劫掠是公认的为自己赢得名望、获取财富的手段之一。 对于那些生活在尚武的社会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封建领主的人来说,有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赢得勇猛战士的声誉、通过捕获奴隶来积聚人力、积累财富。这在维京社会尤其重要: 在维京人的世界里,财富并不是深埋地下或者藏在箱子底的被动累积的黄金白银,而是社会地位、盟友和人脉。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通行的是开放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家庭单位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必须不停地对抗其他人以维护自己的或自家的地位。23 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维持或者提高一个人的地位,随时可用的可支配财产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送出符合他身份的丰厚礼物。毫无疑问,黄金和白银是更受偏爱的财产。24送出的礼物至少要跟收到的礼物价值相当,这种持续的压力导致了“毫无约束”的掠夺嗜好。当然了,在少见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合法掠夺是不存在的,而海盗——不太合法但也没被过多谴责的海上掠夺形式——提供了一种可以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选择。因此,“攫取浮财和奴隶的暴利肯定诱惑了很多人投身强盗行列”25。这种习俗在10—12世纪维京人普通信仰基督教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 中世纪晚期,地中海两岸普遍处于非常虔诚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抗他们”的思想,诠释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是必须——被攻击、被消灭。无论是8—13世纪的撒拉森 海盗,还是巴巴里私掠海盗 ,抑或那些“护教者”,也就是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这些地中海的私掠者们用这种非常简单的二分法来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他们的潜在动机更多带有经济和政治性质。远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会议 上用“神的旨意”(Deus vult)作为口号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一用语就是一个对海上劫掠行为强有力的合法解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基督教骑士会参与这样的冒险。而在“另一边”,也就是伊斯兰世界,由于缺少正规海军,他们更多依靠海盗袭掠来削弱基督徒的海军力量。他们的看法和天主教世界完全一样:穆斯林海盗和私掠者视他们自己为“ghazi”,也就是为了伊斯兰而战的勇士。不消说,这种掺杂着宗教动机的、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海上斗争在印度洋以及远东地区随处可见——只要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正如“神的旨意”所表达的那样,真正的宗教狂热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比如说医院骑士团,他们“轻视生命,随时准备捐躯以侍奉基督”,伟大的英格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如此贴切地叙述道。26比萨和热那亚经常袭击北非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用其收益来光耀上帝,因为他们把其中一部分钱捐给了圣玛利亚大教堂,那时候比萨人刚刚开始着手建造它”27。这些行为充分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宗教被用来合法化海盗行为:“这些侵袭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在跟穆斯林进行一场神圣的斗争。上帝会用胜利、战利品和难以具象化的精神满足来嘉奖他们的努力。”28然而,仅仅从宗教的角度来形容上述冲突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如有必要,强大的经济和政治驱动力可以轻易跨越这种被大肆鼓吹的宗教鸿沟。据说,活跃于15世纪早期的唐·佩罗·尼尼奥(Don Pero Ni?o)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卡斯蒂利亚 私掠海盗,他在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恩里克三世(Enrique III de Castilla)的命令下执行私掠任务,也曾经受到当地政府的邀请,对直布罗陀和马拉加的港口(当时都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的领土)进行过友好的访问。在他的传记中作者指出:“他们带给他牛、羊、家禽、大堆烤面包和盛满了古斯米 和腌肉的平底大盘子;不过,这不表示船长会碰摩尔人 给他的任何东西。”29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卡斯蒂利亚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并未交战,所以穆斯林没有受到他的伤害——不像他们那些生活在北非海岸的兄弟们,正在跟卡斯蒂利亚交战。即便是狂热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也没有把每一个穆斯林都当作敌人——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准则,例外情形肯定是有的。 在穆斯林一方,类似的机制同样在运转着。尽管私掠被视作陆上“圣战”(jihad)的海上延续,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理论上也算是为伊斯兰而战的勇士,很多希腊人、卡拉布里亚 人、阿尔巴尼亚人、热那亚人甚至犹太人也叛逃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倒不一定是由于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激发出来的宗教狂热(大部分叛徒并没有真正皈依),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贪婪和快钱的诱惑。30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活跃于14世纪的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埃米尔”乌穆尔帕夏(Umur Pasha)。乌穆尔帕夏作为一名伊斯兰战士是无懈可击的,他因更喜欢“送法兰克俘虏的灵魂下地狱”而不是留着他们换赎金的作风而闻名。教皇克雷芒六世因为他的危险行径,亲自向其宣战。但这并不妨碍乌穆尔帕夏为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及其继任者约翰六世效命,执行私掠任务。尽管《乌穆尔帕夏史诗》(Destan d’Umur Pasha)的作者在这篇2000行的长诗中颂扬了帕夏的一生,但他还是忙不迭地补充道:“[对]皇帝和他的儿子像奴隶般顺从。”显然在掩饰帕夏对于“真正的大业”公然的背叛——想必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原因。31 1.一部海盗百科全书,全方位解读海盗的前世今生,真实再现1000多年海盗史。 2.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彼得·莱尔力作,《金融时报》《泰晤士报》重磅推荐,《选择》杂志2019年zui佳学术书籍名单。 3比《海贼王》更传奇,比《加勒比海盗》更刺激,揭示海盗真面目,如何影响海洋帝国与世界格局。 4这是一本权威性和教育性的书,世界领先的海上安全和反恐专家以全新视角审视历代海盗。 5.拨开历史迷雾,探索海盗世界的法则,追逐统治海洋的梦想。 真实领略大航海时代的残酷真相! 6从中世纪的维京人一直讲到现代的索马里海盗,深入地探讨了海盗的劫掠动机和发展过程。 ? 7.盗有关的图书、电影和游戏:《海贼王》《金银岛》《黑帆》《加勒比海盗》《基德船长》《大航海时代》…… 8详尽考察全球范围内的海盗历史,深刻分析海盗屡禁不绝的政治因素,揭示海盗背后的隐藏身份——海洋帝国的先锋、刺客、间谍。 9.盗为什么会出现?又为什么屡禁不止?历史上的伟大海盗次第登场,伊丽莎白女王竟是海盗之王? 本书获誉 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读这本书。 ——《金融时报》 在这项信息丰富且很有趣的研究中,莱尔追溯了全球海盗历史,明智地引用了一系列历史学家和资料来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泰晤士报》 在他生动的海盗史中,莱尔发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一些惊人的连续性。 ——《外交事务》 对历代海盗行为的开创性调查。莱尔详细分析了海盗行为的原因,他揭示了在大多数历史上被忽视的海盗行为,他还为索马里沿海、马六甲海峡和几内亚湾最近的袭击事件提供了专业知识。 ——大卫·科丁奇(《黑旗之下》) 世界领先的海上安全和反恐专家之一以全新视角审视全世界历代海盗的行为。莱尔抛开了过去那种笼统的谴责和厚颜无耻的浪漫化的诱惑,找出了这个古老职业的核心永恒的模式。这是一本权威性和教育性的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克里斯·E.莱恩(《掠夺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