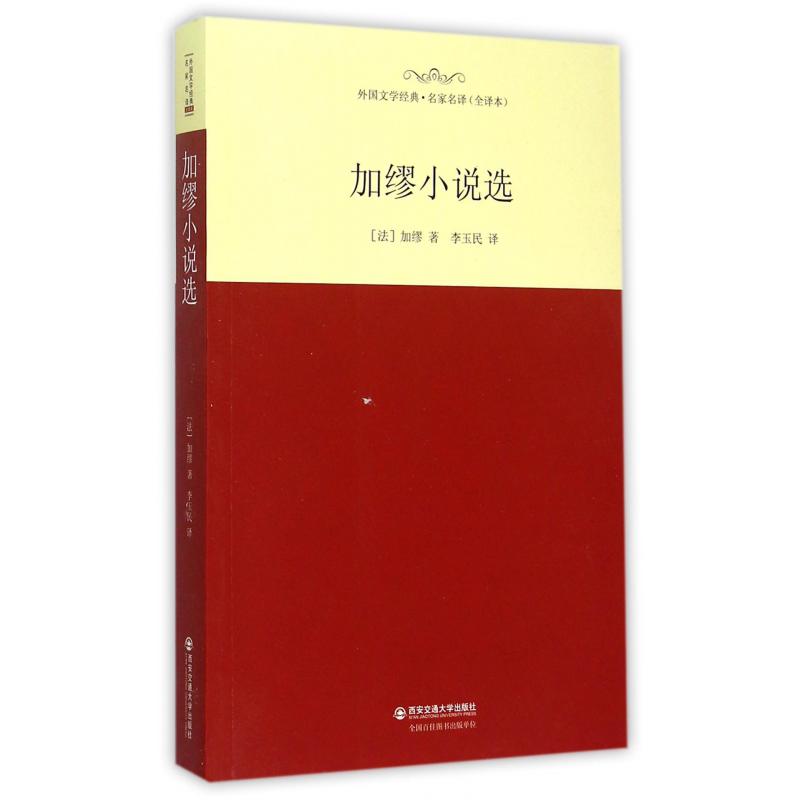
出版社: 西安交大
原售价: 33.00
折扣价: 22.10
折扣购买: 加缪小说选(全译本)/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
ISBN: 9787560554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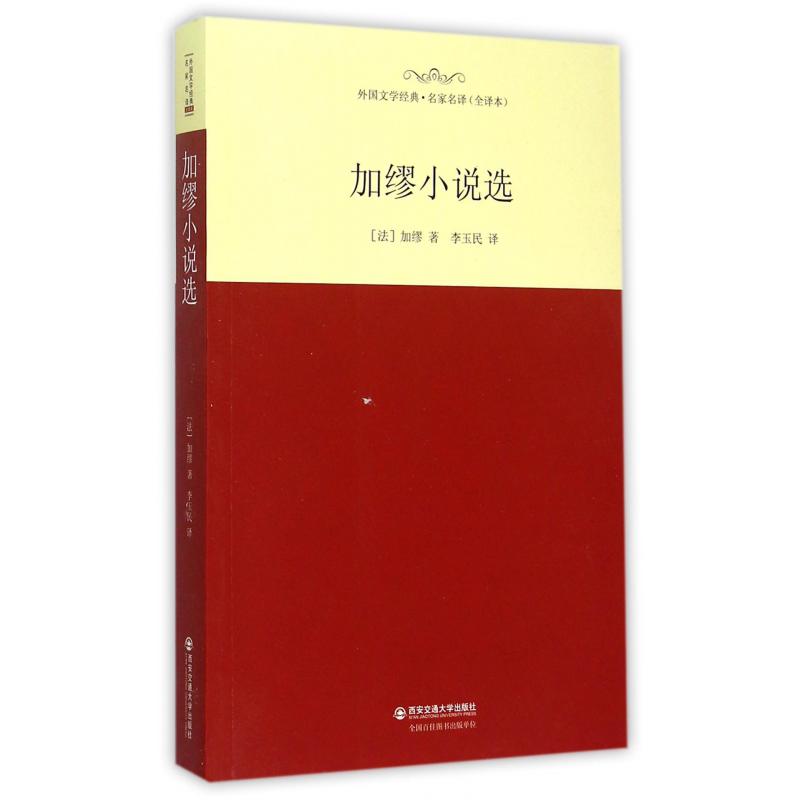
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母亲为西班牙人。父亲在一战中死去,加缪与其母在贫民区艰难度日,后于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1935年,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二战期间投身法国抵抗运动,因其创作的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一举成名,此后又发表小说《鼠疫》、《堕落》和短篇集《流放和王国》;戏剧作品有《卡利古拉》、《正义者》,此外还有散文《婚礼集》、《正反集》及论文《西西福斯的神话》等。未完成长篇小说《第一个人》在其死后出版。 加缪早年曾深入钻研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的著作,他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存在着深刻的荒谬性,我们赖以存身的这个世界是冷漠的和不可理解的,而个人面对荒谬的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在创作上,加缪追求情节的自然铺陈和词句的精确与完美,语言简净、明朗、毫无藻饰,但在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却蕴蓄着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李玉民,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64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到法国勒恩大学进修两年,后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三十余年,译著五十多种,约有一千五百万字。主要译著:小说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等;戏剧有《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诗歌有《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诗选》等六本作品。此外,编选并翻译了《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主编了《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在李玉民的译作中,有半数作品是由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李玉民“译文洒脱,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柳鸣九语)。
第一部 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 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 。”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 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 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 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 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 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 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 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 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 ,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 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 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 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 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 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 月前他的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 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 ;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 。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 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 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 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 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 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 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 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 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 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 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 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 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 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 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来说,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 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 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 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 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 ,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 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 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 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 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 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 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 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 ,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 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 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 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 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 去,他们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 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 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 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 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 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 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 。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 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 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形 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 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 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 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 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 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 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 。”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 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 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 :“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 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 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 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 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 ,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 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 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 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 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 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 身,对门房说:“您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 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P2-4